文· 杨杨 “以聪明才智、能力而言,我不过中等以上,比我条件好的人多的是。”由于相信自己能力有限,“所以我都要借别人的力来达成一些共同的目标。” 施振荣对自己的这句描述,或许是对他能建立“泛宏碁系”、影响整个IT产业的最好解释。 寰宇电子创办人、也是施振荣第一任老板的邱再兴此前曾说:施振荣算是台湾企业界难得的“异数”。许多企业家的成功特质在施振荣身上都不明显:以治军严谨而言,张忠谋更胜一筹;而彪悍霸气也不及郭台铭;城府谋略上则难敌曹兴诚;林百里在专注精研上则更为出色。 或许正是“宽容温厚”的特点,成就了施振荣。他的鹿港老乡吴世雄,曾经用几近崇拜的语气评价施振荣:他的心态已经到了无所求的境界,“他放得下”。 享受大权旁落 1992年,施振荣就在宏碁内部实行了“群龙计划”。这个计划就像今天联想控股以及柳传志在推动的“联想之星”一样,旨在培养100个总经理。“那时候我鼓励不要理我,我还特别强调我就是要享受大权旁落。”施振荣说。 这一想法的背后,有这样的逻辑链条:若不借力他人,“就没有办法把我的力量再扩大,这样即使做到死也就那么一点点大。”施振荣说。但要借力他人“就要和人合作”;而在合作过程中,“要给对方足够的空间,甚至是允许他有很多犯错的机会”。 但在“家天下”的华人企业里,这种分权简直就是神话。“我的个性也不是天生的,是花了很长时间才建立起来的。”施振荣也坦承,在心理层面上这也是一个自我挑战的过程。“我训练自己的办法很简单,就是不想要把自己累死。” 为此施振荣在宏碁推行“人性本善”的观念,在其所著书中也一再论述信任之道。“要不断地相信人,因为由相信人得到的利益更大。”施振荣说,“遇人不淑在所难免,你的筹码就是万一遇人不淑的时候你受的伤害是可以忍受的。我算的是总结果,只要风险控制好就行了。过去就过去了,碰到类似的东西我会更小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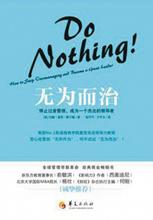
其间施振荣也尝过苦头。宏碁1989年上市时,很多人都警告他,不能让主管持有可流通的股票。他执意那么做的结果,是很多主管在宏碁上市之后陆续卖掉手中持股,去外面自创公司,甚至成为宏碁的竞争对手。 对于离开者,施振荣说“人人都有机会”,虽然施振荣一直惋惜于施崇堂的出走,后者一直被认为是最好的接班人。即便如此,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剑拔弩张,为了减少施崇堂离职对公司带来的冲击,“我们在沟通后,他以赴美国进修为理由离职”,以便顺利进行工作交接。甚至施崇堂后来带领华硕来找宏碁要投资时,“我也想投。”不过宏碁内部有不同的意见,认为不能鼓励公司内部的人不留下来发展或在内部创业,反而出去创立了公司又回来要公司来投资。 “我没有败过” 施振荣从来不避讳谈论自己所犯过的错误,并将过去失败的经验对外分享。在其退休之前,他就已经把自己的每一次失败都交待得清清楚楚了。 1991年,宏碁面临成立以来的首度亏损,甚至外商银行业采取了抽紧银根的动作。为化解公司成立以来面对的最大危机,因此启动了第一次的企业再造,这个“再造宏碁”的过程对施振荣而言,是创业以来经历过最大挑战。当时宏碁甚至卖掉了一些土地与德碁的持股以换取现金流,渡过危机。 “那时候媒体还给我颁过一个奖,说我们反败为胜。”但施振荣感觉说“我们并没有失败”,“我认为这都是更上一层楼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我必须要经历的。”即使当时,施振荣也没有失去过信心,“我每一步都走得很踏实,踏实才不会害怕。” 他认为造成问题的,必然是过去的决策发展造成的,“当时的决策是我自己选的,我也不能怪别人。解铃还须系铃人,我不后悔。”对于施振荣而言,过程性的失败是达到目标的必经之路,“我有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这条路走不通,我可以放弃,再换条路,总会有走通的时候。”如果自身的情况以及公司的状况跟不上,“那我就少做一点。” 因此,即使1991年、1992年在宏碁生死攸关的关口,施振荣的内心斗争也很少。“当下我就采取了一些行为。”而之所以这么做,也是基于从创业之初,施振荣就认定企业不是“自己一个人的”。“大家有共识,互信基础扎实,所以在发生变化时,也不会因为没有共识而不能团结在一起。”施振荣说。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