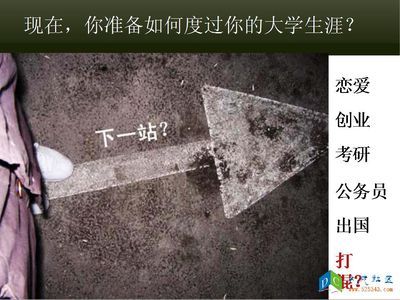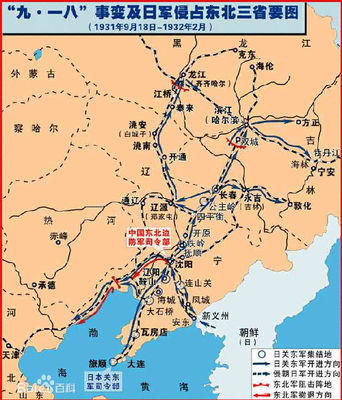一段时间以来,高等教育界内外流行着一种说法,即“大学校长不一定是一流学者”,只要从事过学术工作并懂得学术规律即可;还有学者甚至提出,必须由“二流学者当校长”,理由是一流学者当校长,容易刚愎自用等等。 当然,我们首先需要界定的是究竟什么是“一流”。但我想,无论怎样界定,所谓“一流”的学者,就应该是在其所从事的学术领域已经取得了为学术界公认的成果,被认为是该学术领域的杰出人物。 如果能够对“一流”的概念达成这种共识,那么稍加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所谓“大学校长不一定是一流学者”、“二流学者更适宜当校长”这样的说法很难站得住脚。 一方面,我们可以不去质疑类似的说法有多少调查数据作支撑,也可以不去抱怨类似说法对当今很多(不说全部了,当然也包括院士级别在内的)校长学术水平的不尊重,但另一方面,我们却不能不追问:校长不一定非是一流学者的学理出自何处?所谓“二流学者更适宜当校长”的依据又何在? 当然,上述类似的说法,其前提都来自国内大学。那么,我们在这里不妨换一个视角,看看我们高等教育近年来主要的学习榜样——美国大学的情形如何。 只要上美国各大学的网站去浏览一下就可以看到,校长都有简介公示于众。逐一看过,我们就很容易得出如下的结论:美国顶尖大学的校长绝对都是一流学者。让我举一个例子吧。 德鲁福斯特(Drew Faust)在2007年7月走马上任成为哈佛大学校长之前,就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主要研究领域在美国南方与内战史。她1968年毕业于布莱恩摩尔学院,1971年和1975年分别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在到哈佛之前,曾在宾大工作了25年。在宾大期间,1984年升任教授。在1982年和1996年,她两度荣获宾大的“杰出教学奖”。她出版于1996年的第五部著作《创造之母:美国南北战争中南方的蓄奴妇女》,获得了1997年美国历史学家协会的“弗朗西斯帕克曼奖(Francis Parkman Prize)”,该奖是奖给该年度美国主题的最佳非小说类著作的。1996~2000年期间,福斯特曾担任宾大美国文明系的系主任,2001年1月到哈佛大学创办拉德克利夫高级研究院任首任院长。 在2007年当选哈佛大学校长之前,福斯特于1994年在宾大时被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而在1992~1996年,她曾担任美国历史学研究会的副会长,于1999~2000年担任美国南方历史学研究会的会长。 到哈佛之后,福斯特继续教书和写作。而她在就任哈佛校长之后于2008年出版的第六部著作《这个痛苦的共和国:死亡与美国南北战争》,分别获得美国全国图书奖的提名奖和普利策奖的提名奖,并且被《纽约时报》评为2008年度“十佳书目”之一。 实际上,像福斯特这样的一流学者担任美国顶尖大学校长的现象,在美国具有普遍性。再略举几例: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列文(Richard Levin)是著名的经济学家、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艾美古特曼(Amy Gutmann)是著名的政治科学家与哲学家、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博林格尔(Lee Bollinger)是著名的法学家、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校长雪莉提尔曼(Shirley Tilghman)是著名的生命科学家、美国科学院(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院士…… 我们都知道,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美国科学院在世界上都具有很高的声誉。一名学者进不去或许并不影响他/她的学术地位,但只要能够进入,作为学者,无疑代表着他/她的学术水平是一流的。 我想,一位一流学者在成为校长之后,更多地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甚至有可能必须要牺牲自己一流学者的才能,是可以理解的,甚至也是应该的。我们在为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学术而感到遗憾的同时,也为他们全力以赴地带出一所好的大学而让全体师生乃至社会受益而感到欣慰。 由此观之,一言以蔽之,大学校长应该是一流学者,而顶尖大学的校长则必须是一流学者。绝不能因为国内个别(哪怕是一些乃至很多)一流校长的刚愎自用,就一定要得出“一流学者不宜当校长”这样的结论。在高等教育改革的道路上,这一点当不该再有疑问。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