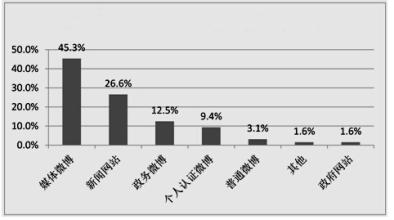“我想着,不就砸了两块玻璃嘛,有什么大不了的。”曹中泽说,当他被关到看守所后,他终于明白,公安局的玻璃和普通人家的玻璃是不一样的。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晓 | 贵州瓮安报道 17岁的范宗敏清晰地记得自己在2008年瓮安“6·28”事件中的“壮举”––––当天晚上10点多,他挤在示威的队伍中在瓮安县政府、县公安局门口看热闹。熙攘的人群中,范宗敏先是听到一个老师模样的人喊“砸”,此时,他仍在观望,没有动手;紧接着,有人放出话来,说是有学生被警察抓走了,愤怒的人们高喊着要求放学生。范宗敏眼尖,一下认出了当时的县公安局局长。他一个箭步冲上去,“快把学生放了!否则8943;8943;”范宗敏恶狠狠地挥挥左手中的汽油瓶,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 午夜,骚动的县城逐渐回归于平静。范宗敏的手腕上多了一副手铐,在黑暗中泛着冰冷的光。 6月29日凌晨三四点,范宗敏被带到了拘留所。 接下来的几天,更多和范宗敏同龄的孩子进了拘留所。经查,“6·28”事件中,直接参与打砸抢烧的违法青少年有104人,其中在校学生96人(未成年人82名),辍学者8人。 每个问题学生背后都有一个问题家庭 “后悔?当然后悔,那时候小,幼稚。”2010年4月底,范宗敏坐在家门口的板凳上,略有些窘迫地评价着两年前的自己。 这是一个身世堪称悲惨的孩子。出生6个月时,范宗敏的父亲去世了。很快,母亲把他丢给了爷爷奶奶,改嫁外地。“别人说我的身高像我爸,长得像我妈。但我对父母没有概念,爷爷奶奶就是我的父母。”这个17岁的大男孩“混搭”着满是污渍的红西装、蓝裤子、白球鞋,目光落在不远处一位担着柴火的老妇身上。那是他的奶奶。 七八岁时,范宗敏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了自己的母亲。此后不久,母亲病逝。 在乡下上完小学后,“孤儿”范宗敏跟着爷爷奶奶搬到了瓮安县城边上的王家庄,在瓮安县职中的初中部读书。 “我在乡下学习很好,还考过全乡的前十名。到县城上初中后,成绩就不行了,平常也没什么朋友。”范宗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初中时,他往往骑着车子上学,推着车子回家,“因为轮胎的气被人家放了。” 范宗敏不打架,依旧独自一人上下学,沉默并孤独着。此时,一个叫“报复”的词在他的心里生根、发了芽,“我想着有一天一定要以牙还牙。” 终于,2008年6月28日,范宗敏的积蓄已久的“报复”一股脑地喷发出来。 17岁的商崇新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如果父亲还在世,我绝对不会走了弯路。” 7岁那年,商崇新的父亲因为车祸去世,“爸爸去世的时候我还太小,没什么感觉。后来长大了,突然明白自己失去了最亲的人。那种感觉太难受了,形容不出来。” 母亲冷云忙着做运输生意,顾不上管他,因此商崇新同样是由祖辈拉扯大的,“直到我上初中,我妈才开始管我,而且一下子管得很紧。”被“放养”惯了的商崇新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 “我和一些社会上的小混混关系很好,虽然没入什么帮派,但如果有人欺负我,总有他们罩着。”商崇新低头摆弄着衣服拉链,声音很低,“我以前脾气很差,一个星期最少要打三次架。这些,我妈都不知道。我以前都不和她说话,后来才勉强说几句。” 商崇新说,他有时会梦到父亲,醒后又不记得他说了什么。有一次,他和朋友在酒吧里喝了很多酒,喝得醉了,想起父亲,跑到大街上嚎啕大哭,没有人知道他在哭什么。 “每个问题学生背后,都有一个问题家庭。”瓮安县政法委副书记王登华告诉本刊记者。 瓮安县雍阳镇政法委书记龙云告诉本刊记者,在雍阳镇,参与“6·28”事件的未成年人有36人,其中有十几个是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 晚上放学校门口有警车徘徊 顺利考上高中的龙家翔并不认为在单亲家庭中长大,对自己有什么影响。4岁那年父母离婚后,龙家翔跟父亲去了江西,母亲带着另两个孩子留在瓮安。直到2005年,母亲才到江西去看了看他。 龙家翔说自己并不是很喜欢读书,小时候,父亲打麻将,他跟着去。父亲赢了钱,他就拿上几块出去买东西吃。有两三次,他攒够了路费,想要到瓮安找母亲,都跑到了车站,还是被父亲发现,拽了回去。 2007年,龙家翔退了学,做起了眼镜加工,拿着不到1000块钱的工资。2008年,他到瓮安玩,看着弟弟去学校报到,自己突然眼红起来,选择了留在瓮安上初中。 “回瓮安后,我们管他很严的,让他好好读书,别在外面打架。”母亲胡玉凤告诉本刊记者。这位母亲努力弥补着儿子缺失多年的母爱。 胡玉凤最担心儿子跟社会上的帮派走得太近,“‘6·28’之前,瓮安的社会治安太差了。” 成立于1988年的“玉山帮”从几个无业青年结拜发起,逐渐壮大为瓮安县首屈一指的帮派。此外,在“6·28”事件发生前,活跃在瓮安的还有“姨妈会”、“鸡家帮”等多个帮派。 瓮安县的一位官员向《瞭望东方周刊》分析,此前,帮派的日益壮大,和政府的软弱和失语有直接关系,“他们之间也互相利用。比如说你作为官员,刚调到某个地方工作,你了解到这个地方帮派势力很大,你要是想把你的工作做好,就可能会动一下脑筋,与其去打击它,还不如去亲近它,互相利用。比如因为宅基地的问题,政府协调不了,也许和帮派大哥说一下,他去吼一声,就解决问题了。而且政府里有很多人也是那个帮派里面的,即使他不是,帮派里也有一些是他的朋友。以至于发展到最后,很多学生都入了帮派。” “我们这些学生不可能主动拉帮结派,多半都是被胁迫的。”瓮安县未成年人帮教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帮教办”)综合科科长卢金明向本刊记者透露,他教过的一个学生曾经愁眉苦脸地找他,说是有黑社会拉他入伙,如果不从,就得每天交保护费。 参与了“6·28”事件的曹中泽就被帮派拉拢过,但他并没有加入。“不过,我和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好朋友,一起玩的时候,谁被欺负了,其他人就都过来帮忙。打架的事被爸妈知道了,就会挨揍。但下次,还会偷偷跑出去打。”曹中泽说,前几年在瓮安,大街上“开火”是常有的事。

2010年4月,本刊记者注意到,每天晚上学生放学时,校门口都会有两三辆警车徘徊。 “不就砸了两块玻璃嘛” 2008年6月28日下午两三点,在人群中的曹中泽把一块石头掷向县公安局办公大楼的玻璃后,扬长而去。那时,曹中泽在瓮安三中读书,“6·28”事件的导火索李树芬,正是他的同班同学,“她学习一般,人还不错。但我砸玻璃,不是想打抱不平,就是看到那么多人都在砸,觉得好玩。” “我想着,不就砸了两块玻璃嘛,有什么大不了的。”曹中泽说,当他被关到看守所后,他终于明白,“公安局的玻璃和普通人家的玻璃是不一样的。” “一贯听话”的龙家翔则趁乱搬走了一台电脑的主机,究其原因,也是觉得“好玩”。 “我当时和几个朋友正打麻将,他就搬着电脑(主机)进来了。”龙家翔的母亲胡玉凤至今说起来还有些哭笑不得,“他说是他在现场拣的,我一看好气哦,让他赶紧给人家送回去,我那几个朋友也告诉他,这是违法的。他又把机子搬了回去,但是当时现场很乱,人那么多,他也不知道要还给谁。” 7月7日,警察把龙家翔从家里带走了,先是在刑侦队呆了24个小时,之后进了看守所。 “一进去,就是一顿暴打,那是见面礼,大家都一样。”龙家翔说着,白净的脸上掠过一丝恐慌,“之后也有人打我,但我从来不还手,怕再背上什么罪名。”龙家翔在看守所里读了些法律书后估计,自己会被判五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孩子也是事件的受害者 在看守所待了128天后,龙家翔被提前放了出来。他更意外的是,自己的“案底”可能被洗清。 瓮安县政法委副书记王登华向本刊记者透露,“6·28”事件平息后,一些家长在之后的座谈会上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孩子有了犯罪记录,以后升学、当兵都会受影响。” “我们在2008年11月份,萌发了消除这些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的想法。更何况,当时有几个学生眼看着就要参加高考,不能让他们有这个心理包袱。”王登华表示。 经过一系列调研和专家论证后,2009年6月,瓮安县委制定了《关于对“6·28”事件涉案未成年人违法及轻罪犯罪记录消除的指导意见》等规范性文件,就未成年人违法及轻罪犯罪记录消除的政策、条件、方法、程序等进行了规范。 瓮安县委政法委员会的统计数字显示,截至2009年年底,参与“瓮安事件”的104名涉案青少年中,已有50名青少年违法及轻罪犯罪记录被消除。 “这种消除不是无条件的。”王登华介绍说,“首先,消除的对象是未成年人;其次,他是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的轻罪犯罪;最后,他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不大。”据了解,目前,只有当时处理案件的司法机关留有这些未成年人的案底,在他们的其他档案中,则并无这一犯罪记录。 “当然,一旦他们中的一些人再犯案,之前消除犯罪记录的决定则要被撤销。”王登华补充。 瓮安县雍阳镇政法委书记龙云认为,之所以拿瓮安作试点开始这一司法改革,是由于“6·28”事件的特殊性,“当时很多参与的学生纯粹是凑热闹,他们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就冲进去了。这和社会、学校、家庭都有很大关系,不能只让学生为他们一时的盲目埋单。其实他们中大多数是这次事件的受害者。” 尽管瓮安县消除未成年人违法及轻罪犯罪记录的做法得到了中央高层的肯定,但王登华承认,这一做法在现行法律中很难找到支撑点,“很明显,这是和《刑法》第一百条相悖的,倒是能从《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找到依据。我们这次只是一个尝试,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如果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则需要进一步完善,或修改现行法律也好,或重新立法也好。” 《刑法》第一百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 “从法律上来说,确实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支撑点,但法律的精神已经有这方面的趋势了。”瓮安县帮教办一位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被当作绝密的问题少年“黑名单” 在消除未成年人违法及轻罪犯罪记录之前,配套的帮教工作也在2008年末开展起来。而今,“帮教”显然成了瓮安县的一个宣传亮点。2010年4月27日,《瞭望东方周刊》在瓮安县采访期间,就听到政府门前的喇叭中,用了近10分钟来宣传帮教工作。瓮安四中则将本校的帮教工作结集成册,用以存档和宣传。 “我们搞了一个‘321’工程,”瓮安四中副校长刘金巧解释说,“‘3’指帮教形式,即一名学校领导、一名教师、一名帮教对象,形成一个帮教小组;‘2’指帮教内容,即重点抓思想道德教育和行为规范教育;‘1’是指帮教平台,即搭建活动平台,使帮教工作有一个可支撑的载体,比如我们组织的十佳歌手比赛、书法比赛等等。” “出来后学校、镇上都找我谈话、家访。”曹中泽称,“我出来之后转变挺大的,有了帮教,基本上所有和我一样的人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如果没他们帮教,估计顶多有八成。” 瓮安县帮教办综合科科长卢金明告诉本刊记者,目前,帮教工作已经扩展到针对问题青少年、社会不良青少年身上。几个乡镇统计下来,卢金明手里拿到了一份299人的“黑名单”,“这个数字还不够准确,我们需要进一步核实和甄别。” 卢金明说,上世纪90年代,就有人提出过“问题少年”的概念,当时,他是坚决反对这一提法的,“我那时候认为,我们的学生有什么问题啊,就是学习差一点,某些方面表现差一点,不应该从教育的角度把他们列为问题生。”但十几年后,卢金明无奈地承认了这一说法,“随着社会的发展,留守孩子、单亲家庭的孩子越来越多,确实存在不少问题。” 所谓的“黑名单”是一份绝对机密的文件。“我们肯定不会把它捅出去。”卢金明说,甚至在和“问题少年”谈话时,帮教人员都会尽可能小心着不让对方发觉自己已经上了“黑名单”,“谁都不愿意自己被扣上这个帽子,我们只能暗中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在生活上多关心他们一些。” “你会在另一个舞台上采访我” 经过“6·28”事件后,商崇新终于改过自新了,“如果当时成熟一点,也不会失去半年自由。可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我以后判无期、死刑都是有可能的。” 但他还是不喜欢学习,一上课就打瞌睡。在瓮安县职中上了一段时间后,他退了学,去学开挖土机,“我觉得这个想法挺成熟的,反正上三年下来,我也考不上大学,倒不如用这三年来挣钱。下半年我就可以靠自己的工资吃饭了。” 在这个不大的县城里,商崇新还是会经常碰到以前混在一起的小兄弟,但他说自己几乎不和他们玩了,有时甚至连招呼都不打。 商崇新打算27岁时就结婚。他和现在的女朋友恋爱谈了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了“6·28”事件。从看守所出来后,商崇新觉得自己有了污点,说要分手,但最终还是没分成,“想要找一个合适的人不是特别容易,彼此还是要珍惜。” 父母双亡的范宗敏也没再上学。早在上初二时,他就利用周末学起了装潢技术。2008年10月,刚从看守所出来,他就借了5万块钱,在王家庄开起了一个装潢材料加工厂,自己当起了小老板。“我的成熟和从小的经历有关,好比一棵树,在不同的地方长出来的就不一样。”范宗敏冒出一个还算恰当的比喻。 从看守所出来的龙家翔不久就在学校组织的“十佳歌手比赛”中拿了名次。意外的荣誉让这个男孩迅速找到了人生方向。考上瓮安二中后,他学起了吉他,如今可以断断续续地弹唱《丁香花》,“我毕业后要考音乐学院,你信不信,你会在另一个舞台上采访我。”(注:文中涉案的未成年人及其家长均为化名)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