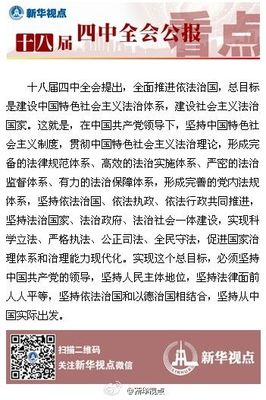易中天
厦门[email protected]
韩非不动声色地说出了人性中的恶
问:儒法两家的分歧,主要就在“德治”与“法治”?
答:是的。儒家主张“以德治国”,法家主张“以法治国”。
问:这个分歧,与他们对人性的认识有关?
答:没错。韩非说,儒家和墨家,都讲爱(仁爱或兼爱),也都讲道德(礼让或互利)。但是请问,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是爱,是道德吗?不是。
问:那是什么?
答:是“利害”。韩非说,长工种地,地主又是送饭,又是给钱,是因为爱长工、讲道德吗?不,是希望长工多卖力气。长工精耕细作,挥汗如雨,是因为爱地主、讲道德吗?也不是,是为了多吃好饭,多拿工钱。所以,开马车铺的都希望别人富贵,开棺材铺的都希望别人早死。这不是因为前者仁慈后者残忍,而是因为没人富贵,马车就卖不出去;没人死亡,棺材就卖不出去。马车铺老板也好,棺材铺老板也好,都不过是为自己打算,没什么道德不道德、仁义不仁义的问题。当然,也没什么爱不爱。
问:人与人,只有利害关系?
答:韩非认为是。因此,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也没什么“礼让”或者“互利”,只有“算计”,甚至“防范”。
问:都是这样?
答:君臣、父子、夫妻,都一样。韩非说,做君主的,为什么要封官许愿、重金悬赏?就是为了收买臣民,让他们为自己卖命(所以易民死命也)。同样,做臣子的,又为什么要尽心尽力,勤劳国事?还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可见君之与臣,无非一个出卖官爵和俸禄,另一个出卖智力和体力,不过买卖关系。这就要算计。于国有利,于己无利的事,臣不会做;于臣有利,于国无利的事,君也不会做。所以说“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
问:父子之间应该有爱吧?
答:也没有。韩非说,寻常人家,生了男孩就庆贺,生了女孩就弄死,因为男孩是劳动力,女孩是赔钱货。可见父母对于子女,也是 “用计算之心以相待”的。
问:夫妻之间也没有爱吗?
答:更没有。韩非说,卫国有一对夫妻做祷告。老婆说,但愿我们平安无事,赚一百束布。老公说,怎么才要这么一点?老婆说,够了!要多了,你就会去包二奶。你看,这不是只有“算计”,只有“防范”吗?所以韩非一再告诫那些君王,千万不要相信别人,尤其不能相信你的老婆孩子。
问:为什么不能相信?

答:因为君王之利实在是太大了,足以让人想入非非,铤而走险。一旦相信别人,没了警惕性,就很有可能给那些乱臣贼子以可乘之机。
问:老婆孩子,怎么就尤其不能相信呢?
答:因为君王的老婆孩子,利害关系最大呀!我们知道,一般地说,一个君王不会只有一个儿子,这些儿子也未必都出自同一个母亲,但继位为君的儿子却只有一个。这个儿子接了班,他的母亲就是太后,可谓子也君,母也君。其他的儿子和他们的母亲呢?子也臣,母也臣。这可是天壤之别。
问:谁当接班人,不是有规矩、有制度吗?
答:那是“天下有道”时的事,“礼坏乐崩”的时候就不好说了,君主完全可能由着性子胡来。更糟糕的是,按照韩非的说法,男人到了五十岁还很好色(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女人过了三十就看不得 (妇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母亲一旦失宠,儿子的储君地位就会动摇。这时,最大的“利”,就会变成最大的“害”。
问:那又怎么办?
答:只有抢班夺权,干掉那好色的、宠爱小老婆和小儿子的在位之君。这个时候,毒酒之类的东西,绞杀之类的手段,可就派得上用场了。王后和太子近在君侧,做起来是很便当的。于是韩非感叹说,既然老婆孩子都相信不得,还有谁可以相信呢?没有了(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
问:这话听起来真让人起鸡皮疙瘩。
答:是啊!韩非可以说是“直面惨淡的人生”,而且是惊心动魄的 “直面”!在中国历史上,似乎没有谁,像他这样说出了人性中恶的一面,而且还说得那么直白,那么冷峻,那么不动声色。这可真是让人难以接受。但是,在读过《韩非子》以后,你不觉得孔子的“克己复礼”有点迂腐,墨子的“兼爱天下”有点矫情,庄子的“自在逍遥”有点轻飘吗?事实上,在韩非这种沉甸甸的冷峻面前,孔子的厚道,墨子的执著,庄子的浪漫,几乎一下子就失去了分量,变得单薄、空洞、苍白无力,甚至滑稽可笑。这就是真实的力量。
问:于是,韩非不再相信人,只相信制度?
答:其实就连制度,韩非也不全信。只不过在他看来,多少能够起点作用的,也就是制度。其余那些,比如思想工作、道德教育、舆论监督等等,全都没有用。
利害与善恶,不过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说法
问:韩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点?
答:因为他想清楚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世界上为什么会有善、有恶。这个问题,我们也应该想一想。想不清这一点,就回答不了前面的问题。
问:怎么想?
答:问动机呀。请问,有人作恶,是因为他们有此嗜好吗?当然不是。那么,反过来也一样。有人做好事,也不是因为他们喜欢行善。
问:怎么就不会有人喜欢行善呢?
答:因为按照辩证法,有人喜欢行善,就有人喜欢作恶。这样一来,我们又得再问,同样是人,为什么会有人喜欢行善,有人喜欢作恶呢?
问:天性。解释为天性,不行吗?
答:不行。人,都是一样的。人性,也都是一样的。不一样,就不能叫“人性”。因此,人的天性,要么像孟子说的那样,是“向善”的;要么像韩非说的那样,是“本恶”的。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一部分人“天性向善”,另一部分人“天性嗜恶”。
问:荀子不是说人性有善有恶吗?
答:那是指同一个人,不是指不同的人。也就是说,在同一个人身上,既有善,也有恶。所以,同一个人,可能会有时候行善,有时候作恶。这又反过来说明,作恶和行善,决不是天性使然,不是某些人天生喜欢行善,某些人天生喜欢作恶。
问:那是什么?
答:利害使然。韩非说:“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也就是说,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利之所至,趋之若鹜;害之所加,则避之惟恐不及。这是人之常情。如果利害关系不大,或许还能讲点道德,守点规矩。一旦诱惑无法抵御,或者危害难以承受,恐怕就顾不上什么道德不道德,甚至法令不法令了。
问:有证据吗?
答:有,韩非就讲过这样的故事。这故事说,楚成王先是立商臣(也就是后来的楚穆王)为太子,后来又打算改立他人。商臣就去找自己的老师潘崇,问应该怎么办。潘崇问,你能接受事实吗?商臣说,不能。潘崇又问,你能出国避难吗?商臣又说,不能。潘崇再问,你能发动政变吗?商臣说,能。结果商臣带兵逼宫,请他老爸上吊自杀了。这个商臣,岂能不知“杀父弑君”是“罪大恶极”?当然知道。但是利害关系太大,也就只好对不起。
问:做好事,也是出于利害关系吗?
答:在韩非看来也是。地主给长工送饭,长工帮地主干活,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自己嘛!只不过立场不同,价值判断就不同。对于长工来说是“善”的(比如送饭),对于地主来说却是“利”。反过来也一样。由此可见,利害与善恶,不过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说法。在己为利害,在人为善恶,如此而已。硬要讲道德,也只能说,利人利己是善,损人利己是恶。但不论善恶,总归要利己。
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呢?
答:我们认为,这个可以有。韩非认为,这个真没有。
问:于己有利,才做好事?
答:是啊!在韩非看来,人不为己,谁肯早起?所以,要鼓励人们做好事,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好人有好报。要防止人们做坏事,也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恶行有严惩。
问:明白了,还是赏罚二柄。
答:没错。所以,就算要进行道德教育,也得把利害关系说清楚了。要告诉大家,做好事其实对自己有利,做坏事其实对自己不利。因为你帮别人,别人也会帮你。你害别人,别人也会害你。是得到祸害好呢,还是得到帮助更合算,诸位自己想吧!
问:这话我怎么听着耳熟啊?是墨子的观点吧?
答:正是。讲功利,讲实惠,承认趋利避害的合理性,是墨家和法家的共同之处。不同的是,墨子以利害说道德,韩非以利害说制度。也就是说,在墨子看来,正因为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所以要讲道德。为什么呢?因为你也不讲道德,我也不讲道德,人人损人利己,结果是大家都受损害。相反,如果都讲道德呢?人人都能得到爱和帮助,包括你自己。
问:这不是很对吗?法家为什么不赞成呢?
答:因为墨子所说,不过道理。道理,谁信呀?还是得动真格的。或者说,必须让人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好人有好报,恶行有严惩。谁能保证这一点?制度。
问:制度就那么可靠吗?
答:也有靠不住的时候。韩非自己讲的一个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这故事说,伍子胥逃出楚国,被守关的官吏捕获。伍子胥说,大王之所以通缉我,是因为我有一颗宝贵的珍珠。不过这颗珍珠现在已经丢了。你要是把我送到大王那里去,大王问起来,我就说珍珠被你私吞,你看着办吧!结果那守关之吏把伍子胥放了。按说,楚国也是有刑法和制度的吧,怎么不起作用了呢?道理很简单,再完善的制度,也要由人来执行。所以,只有“良法”,没有“好人”,天下还是不能太平。如果只讲制度,不讲道德,那就还会更乱。
以法治国,以德育人,也许能行
问:这个说法奇怪!制度好,人不行,顶多也就是执行不力,怎么还会弄得更乱呢?
答:因为世道在人心。人心坏了,世道岂能不坏。
问:依靠制度来管理社会,就会把人心搞坏吗?
答:孔子认为会。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道之以政),刑罚来规范(齐之以刑),结果只能是“民免而无耻”。
问:什么叫“民免而无耻”?
答:就是人民不敢犯罪,但没有羞耻心。这就仍然有可能作恶,有可能犯罪,尤其是在法治不到之处,执法不严之时。比如楚国那个守关之吏,还不是执法犯法,把伍子胥放跑了?还有《水浒传》里的宋江,干脆给“通缉犯”晁盖通风报信。这种事,我们见得多了。
问:完善制度,严格执法,不就行了?
答:不行。只要没有羞耻心,就总会有人想犯罪。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想,有时候比“做”还恐怖。单纯依靠制度的结果,既然是“民免而无耻”,岂非培养出一大批时刻都在“惦记着”的“贼”?更何况,有禁,就会有人犯禁。而且,越是禁,就越是有人想犯禁。亚当和夏娃,就挡不住这诱惑嘛。这样说来,法家的“以法治国”,就简直是拿着肉包子打狗,是教唆犯罪了,所以儒家坚决反对。
问:那又该怎么办?
答:儒家认为,还得靠道德,靠道德的力量。孔子说,用道德来引导(道之以德),礼仪来规范(齐之以礼),人民不但知羞耻,还能自律(有耻且格)。自律,就不但“不敢犯罪”,而且根本就“不想犯罪”、“不会犯罪”。换句话说,只做好人,不干坏事,也不“惦记”。
问:明白了。在孔子看来,讲法治,靠制度,只能争取人们不做坏事;讲道德,靠教育,才能保证大家都是好人。是不是这样?
答:是。
问:儒家的主张好,标本兼治嘛!
答:好是好,可惜做起来难。
问:为什么?
答:因为道德只能诉诸良心,而良心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别人管不了。比如孔子的学生宰予反对 “三年之丧”,孔子也只能去问他,父母去世不到三年,你就吃细粮穿丝绸,心里好过吗?宰予说,好过呀!结果孔子毫无办法,只好气呼呼地说,你心安理得,你就那样做好了。你看,孔子的道德主张,连自己的学生都治不了,还能治国?
问:这么说,道德是不能治国的?
答:不能。不但不能,还有副作用。因为你要“以德治国”,统治者或领导人就得率先垂范。这样一来,君王就得是“圣人”,官员就得是“贤人”。他们都必须高风亮节,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才能以德服人,也才能真正推行礼乐教化,对不对?
问:对呀!这有什么不好吗?
答:做得到当然好,做不到呢?也只有一个选择──作假。事实上,历代王朝“以德治国”的结果,并没能保证他们的长治久安,只不过制造出一代又一代的伪君子。这些伪君子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儒家他们设立的圣贤标准逼出来的。
问:法家的“以法治国”就好吗?
答:当然也不十全十美,但至少有一点可取,那就是他们的制度,是按照常人的标准来设计的。这就比较靠得住。毕竟在这个世界上,圣贤总是极少数,常人却是大多数。可着大多数人的尺度来规范,第一,肯定可行;第二,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因为你把最坏的结果都考虑进去了,已经事先做了防范。
问:你的意思,是不求“最好”,只求“最不坏”?
答:至少,在设计制度的时候,只能如此。实际上,迄今为止,世界上都没有完美的制度,只有“最不坏”的制度;而那些“最不坏”的,又往往比自以为“最好”的好。
问:但是,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你以常人为标准,岂非每下愈况?
答:这个批评有道理,所以儒家的主张也不能全盘否定。而且,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再完善的制度,也要由人来执行。法再好,人不行,还是不行。这就不能再靠“法治”或者“法制”了。历史证明,法家的“以法为教”,也是失败的。
问:那又该怎么办?
答:以法治国,以德育人,也许能行。事实上,道德虽然不能治国,却可以育人;法制虽然不能育人,却可以治国。这就可以相互补充,也能解决只取一面所产生的问题。不难想象,一个国家,如果法制既健全,社会又道德,岂能不长治久安?
问:这样说来,儒法也可以互补?
答:可以,但不能是历代王朝的“外儒内法”、“阳儒阴法”,而应该是分工合作、抽象继承。所谓“抽象继承”,就是只取其合理内核,不要其具体规定。至于“分工合作”,大约可以理解为治国不妨多读法家,育人不妨多读儒家吧。当然,也不能“全盘接受”哦!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