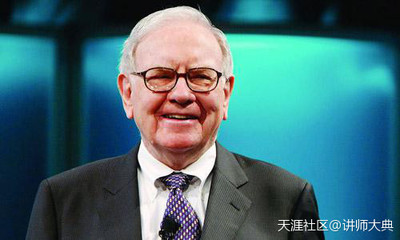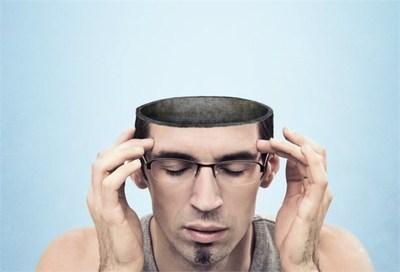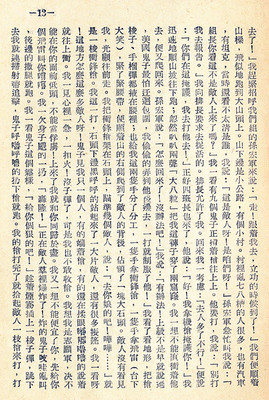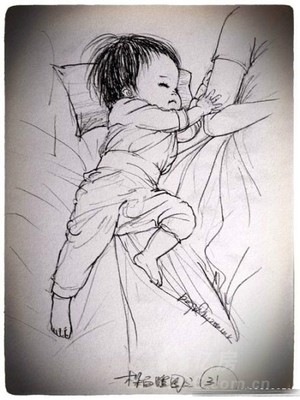杨沛霆 朱厚泽是位高官,又是我的老朋友,回想起每逢一见面就无话不谈,都有“他乡遇故知”的亲近感觉。 当年我们中国科学技术讲学团,请他到会,他总能很快和大家打成一片,说说笑笑,谁都不会想到他曾是贵州省和中宣部这样重要省部级部门的一把手。甚至后来还有人传说,他是耀邦同志物色的接班人。从耀邦同志到厚泽同志,真是一脉相承——正直、厚道、亲民。 有一次,他请我到他家去。我初到中央大领导家里难免显得拘束,他就把我带到他的书房里,指着书架说:“你看,这里还放着你写的书呢!”当时,我的激动难以言表……而且一下子,就把我们之间本很严肃的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拉近了,并很快成为了朋友。 当我在他家客厅,看到我所敬仰的领袖胡耀邦同志的大照片,便一下子就想起耀邦主持中科院工作时,曾到所属所有研究所去看望大家——据称历届中科院一把手,只有他做到了。

那是一个夏天,很热的天气,我穿着背心低头写东西。不同寻常的讲话声音使我一抬头就看到耀邦同志,我马上拿起衬衫要穿上,袖子还没伸进去,耀邦同志立即伸手扶住我,说:我是来看望你们的……那一刻,我真是受宠若惊。 耀邦同志的亲民作风,在厚泽同志身上可谓克隆再现。即使他在担任中宣部部长期间,我们在他身上看到的也只是关爱的友情,而没有居高临下的官气和架子。我多么期望中国的公务员,都能有像他一样的亲民作风啊!每当我看到城管的“小干部”——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他们——从小汽车或大摩托上下来,威风凛凛地把临街叫卖的摊贩赶得满街跑,还把蔬菜水果踩碎的情景,还有什么亲情可言?! 据称,朱厚泽同志到中宣部上任半年多里,只搞调查研究,从不居高指示讲话。后来在一次文化部厅局长会上,即在文革结束十周年之际,他果敢地提出了对不同意见要“宽松、宽容、宽厚”、“不能以言治罪”的“三宽”政策,很博广大知识分子的欢迎。 作为领导的素质,他是优秀的,卓越的。他具有亲民、诚恳、朴实、实事求是、极端负责任的优秀传统干部作风。而且他能独立思考、慎言笃行。与很多传统干部不同的是,他讲话从不用稿子,出口成章,逻辑严谨。他的每次谈话,你都能感受到他的谨慎好学、勤于思考,不随波逐流、且严以律己的学风所感动。有一次,我问他:您离开贵州后,接您班的正是胡锦涛同志,您对他有何印象?他当即告诉我:他比我强!他到贵州第一天与机关同志见面,第二天拜访老领导,第三天下乡调查民情。我到中央工作,认为只对耀邦同志负责,没有及时去倾听老前辈们的意见,这是我的一个错误。他这几句话,至今言犹在耳。 后来,我请他去吉林、海南讲学,他讲课很受欢迎,口才好,阐述深刻。课后,大家知道他曾是中宣部部长,都很惊讶——离他们心目中只讲原则套话,或只传达上级指示的宣传部长相去甚远!而且他摄影艺术高超,我看到他在西南洱海边拍摄的作品:夕阳下一条扁舟静谧地飘荡,让我仿佛感受了一种油画风情。我说你是名副其实的摄影艺术家!他满意地笑了。我知道他陶醉在他创作的艺术创作之中了。 我最后与厚泽同志见面,是今年春节过后。那时他精神还很好,还那么健谈,从国内外形势到国家政策无所不包,他已重病在身,还在关注国家、民族的大事,但谈到自己的病情却一句带过——这让我深受感动。他对民企表示同情,对当今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与发展感到担忧。在我临走时,他又概括了我们30年的改革:“从国家回归社会,从官方回到民间”,可谓异常深刻!在那次谈话中,他对“中国管理模式”的关注与思考,尤其令我信服。我当即表示:在成思危同志领导下,我们要组织大家研究讨论这一问题。他很高兴。 如今噩耗传来,大地空寂,我将默默地去做他未竟的事业,组织好“中国模式的研究”,也算我为纪念他的离世所写的碑记吧……朱老,你安息吧!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