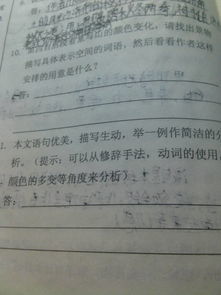(1)想不到家里会收养起一块石头来。

(2)它本来是趴在一个朋友的菜园矮墙上的,木木拙拙,泥头败脑。今年盛夏的一天,去看朋友,正下着雨。也巧,走到它的身旁,雨水正好淋出它的斑斑纹路,竟是一身树的纹理。一头贴墙,千层饼似的灰黑的纹理挤戗着;一头翘峨,剖露着触目的年轮。这样一团的残树朽干,经历雨水会腐烂生蘑的吧?我无意间抬手戳了戳它像是腐朽的纹理,居然钢锉般涩硬。索性掀掀它,更叫我一惊:没掀动。这个木头木脑的家伙,一下惹起我的兴趣,细细打量打量,搓搓手,双手搬它,竟铁一般沉!再看它,翘峨的年轮仿佛是一圈圈的笑。我明白了,这是一块树化石。
(3)我本来是个闲情逸趣不多的人,不喜养花,不热养鸟,也没有收藏的爱好。但是这次却破了例,将这块树化石抱回了家。说真的,对它,我莫名其妙地生出了点喜欢。
(4)等我将它往门厅里一放,就先没了底气:新崭崭的厅里放上土头土脑的它,真是不伦不类、格格不入呢,妻子容忍的笑里分明在说:“扔了吧。”我不敢看妻子的笑,只自言自语着:“先放放吧。”
(5)放是放了,位置却变了又变,先是从冲门处移到了厅旮旯,随后又从厅旮旯挪到晾台上。那天下了班,已是傍晚,夕辉虚弱得无力撑起暮霭的丝幕。我见它在晾台上,正翘峨着头凝望着太阳陨落的地方。它灰黑的纹理也已和暮霭化为一体,只有年轮如眼,审视着朦胧的天地。木石心肠,沉表如坟,真是憨愚到极致了,任何具体的“轰轰烈烈”、大喜大悲似乎都已无法将它惊动。我屏息瞅它,猜想,莫非那数不清的岁月正在它的眉间放映?
(6)躁动的生命,不觉间澄明恬静起来。
(7)有岁月的胸际如云翻飞。我学它举首审视着苍茫的天地,脚下就是永恒之台。
(8)于是,我双手捧着,将它请进耳鬓厮磨的书房。
(9)在这精神的家园里,我好像也成为一棵树,与它一起拥有悲欢的人间和阴晴的宇宙。我们默默地相对着,时间就定格在这种默然里,只有生命灵动异常,羽化为轻盈的万物。常常是不经意间,我们会有絮絮的对话,如风中的杨叶——
(10)“人是高级动物吗?高级在哪里?我是看着人类从无到有的,你们远没有超越从兽性到人性这道鸿沟,如果将人类的心灵一下子撕开在光天化日之下,其丑陋与残忍的情景,将是最可怖的。但是,我又真真地对你们充满着爱与期待。你们的智慧与善良,虽然还嫌稚嫩,毕竟是那样美丽又那样生机盎然。我会耐心地等待,你们不在意有一个旁观者吧?”
(11)“你的根呢枝呢叶呢?它们是在一次天塌地陷的灾难中失去的吧?在这天塌地陷之前,一定是骤雨削去了你的冠、狂风折断了你的干,你不为青枝绿叶生命的永远失去而悲伤吗?这样看来,宇宙不也是残酷的吗?”
(12)“是的,我曾深深地悲伤过,也极度地绝望过。可是,浩淼的宇宙是不会注意到一棵小树的悲伤与绝望的。只是在我跨过悲伤、咬碎绝望,在漫漫黑暗的熬煎中涅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