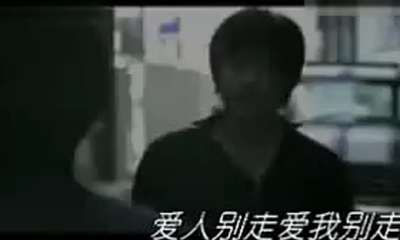那年,她二八年华,清淡如菊。那天,梨花刚白,清明刚过,她着杏黄衫子绿罗裙走上柳陌踏青。柳絮在她身边翻飞,可她纤手一伸,柳絮就轻悠悠地飘远了,她无奈地望着它们。
这时,一只手伸过来,捉住一团柳絮,轻声道:“接着。”
她抬眼,面前是个白衣男子。他的脸上有种洁净的微笑,像阳光一样,他的眉眼拢着一层说不出的潇洒风韵。
她怯怯地伸出手,那团柳絮放在了她手心。柳絮映着阳光,白白亮亮的,如纤尘不染的眉眼在望着她。
她低着头傻傻地望着柳絮不敢抬头,当抬起头时,那男子已走远了。她急了,忙喊:“请问公子是谁?”
远远传来一声清朗回答。她听清后愣了一会儿,对着手里的那团柳絮道:“原来你就是李之仪。”
柳絮在她手心翻了个个儿,随风悠悠飘上高空。怎么也飞不出她的心里。
她叫胡淑修,出身朱门绣户,父亲是朝廷官员,泼洒翰墨,诗词文章皆不在话下。父亲将她也培养成一个女博士,读书吟诗无所不能。
她在闺中看花开花落,看燕子来去,名字却早已传入那些读书人的耳里,成为一段传奇。许多王孙公子踏入胡家,希望成为这朵名花之主。
她却告诉父亲,心中已有一人。父亲问起时,她的眼睛望着窗外,仿佛又一次站在柳陌上,再次面对那人。
她轻轻道:“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
父亲眼睛一亮,拊掌笑道:“李之仪,李才子啊。”
次日,父亲便亲自上门撮合这段美好姻缘。不久之后,她坐着大红花轿,在一个晴朗日子里做了他的娘子。
从此,他们举案齐眉,斗茶填词,在诗词琴声中你侬我侬。他们希望“日日思君不见君,同饮一江水”只是一句清新流白的词,只是他的无病呻吟。可谁知这竟是婚后的一个谶语。
那年他因得罪权臣而入狱,罪名是他将一位大臣的遗稿随意篡改,欺君罔上。
她知道后,哭过伤心过,然后咬咬牙站起来。要洗刷他的罪名,就必须找到那份原稿。她收起泪水,走出深闺,走向车马来往的市井,走入万丈红尘的官场,到处寻找打听着,希望得到一点蛛丝马迹。终于,她打听到有个姓张的官员收藏着那份原稿。
她马上来到张家,敲开那扇朱红大门,对那位官员行万福礼。她流着泪告诉他,自己的夫君李之仪被人陷害,希望有一个证据帮夫君洗脱罪名。她本以为这只是举手之劳,可那人拒绝了。他不会因为她的请求拿出那份原件,得罪权臣。
她哀求着,希望对方能出于良知,出于和夫君的同朝之谊答应下来。可那人坚决拒绝。她心里瞬间梅雨连绵。
带着一颗黯淡的心回到家。没有他的家清冷蚀人,也一寸寸咬啮着她那颗柔软的心。
她望着他用过的一切,砚台,笔墨,想着在这儿他曾写下灵秀的文字。现在它们孤零零的,如同形单影只的她。
飞鸿过,夜月下只留声声啼鸣,她的泪忍不住涌出。她想了想,开始打点家里的东西,包括他们喜欢的古玩。然后,她摘下金钗,褪下玉镯。
第二天,她一副布裙荆钗的样子再次来到张家,把这些东西交给一个看门人,求看门人放自己进去。她说她只想救出夫君。
看门人终于答应了,她悄悄走进张家。那份原件她已打听清楚,知道放在什么地方。她不担心自己的安危,只担心自己一旦被发现,他就永无洗冤昭雪的日子了。
她终于找到了那份原件。她以为可以救他了,一起今生来世白头相随,可以做一对鸳鸯,抛却愁肠漫游于春风芳草池塘。她想,这以后君为磐石,妾为蒲苇,两厢厮守,年年岁岁。可她怎么也没想到,她的愿望仍如飘飞的柳絮。
他虽被洗去冤情,可那权臣难解心头之恨,将他发配到一个叫太平州的小地方。
他单衫伶仃,在子规声声雨如烟里打点包裹,准备远行。而她经过这些波折,已病体支离。他抚着她的手说:“养好身体,我会回来的。”
她轻轻摇头,泪珠零落而下,多年夫妻聚少离多,几多恩爱跌宕坎坷。她不放心他一个人去那么偏远的地方,也怕他将来回来时,家里已人去楼空。她怕到那时,他推门看到的只有帘幕低垂,燕子来去,空屋无人。
与其分离之后永不相见,不如相依相偎老死天边,给他最后一丝温暖。她强撑病体陪着他,坐在一辆青幔车中向远方走去,一直走向她生命最终的驿站。
他拉着她的手,轻声道:“随着我,你受苦了。”她一笑,轻轻地摇头,望着他,一如当年初见时。只是岁月匆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她的鬓边已白发隐现。
岁月无情让人动容。来到太平州不久,她终于坚持不住了。
他曾问过她,为什么两情相悦的人能频频见面,却不能长久厮守?相识那年,嫁娶那夜,她拉着他的手对着窗外明月发誓,她要陪着他生生世世永不分离。
可是,她也有耗尽的一天,如风中烛火摇摇欲灭。她气喘吁吁地对他说:“没陪你走到最后,是我负了你。”
他多想时间能倒回,回到他们初见的那日:江南春晓,乱莺飞舞,他和她相视一笑,牵手走过,慢慢把曾经经历过的一颦一笑,再细细重温,慢慢度过。
可是,一切都结束了,风止了雨停了,落日如终了的曲子般在天边慢慢湮没。他知道没有她的日子,从此自己永远如一个过客,日日行走在感情的苍凉古道上,任马蹄哒哒,敲过青石板小巷,却再没有一扇小窗向他揭开春帷,浅浅一笑道:“你回来了?”
他再次落泪,望着远空。江南,春天已经老透,他的思念却如长江水,永无止息。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