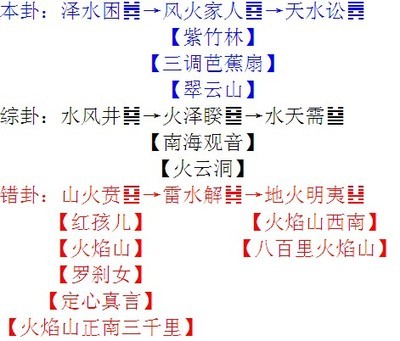后宴丹霄楼,酒中谓长孙无忌曰:“魏徵、王珪事隐太子、巢刺王时,诚可恶,我能弃怨用才,无羞古人。然徵每谏我不从,我发言辄不即应,何哉?”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谏,若不从辄应,恐遂行之。”帝曰:“弟即应,须别陈论,顾不得?”徵曰:“昔舜戒群臣:‘尔无面从,退有后言。’若面从可,方别陈论,此乃后言,非稷、蒐所以事尧、舜也。”帝大笑曰:“人言徵举动疏慢,我但见其妩媚耳!”徵再拜曰:“陛下导臣使言,所以敢然;若不受,臣敢数批逆鳞哉!”
说实话魏征何止是“举动疏慢”,现在的下属也找不出他这样傲娇的。他给领导提议,领导如果不听。领导再说什么,他就爱理不理的了(辄不即应)。领导说下次当面先别说出来,背后慢慢说,人家也不同意。这还是领导酒宴上吐槽给大舅子听的,大舅子长孙无忌还没答话,魏征就来抢答了。
“征状貌不逾中人,而有胆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颜苦谏;或逢上怒甚,征神色不移,上亦为霁威。尝谒告上冢,还,言于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严装已毕,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实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辍耳。”上尝得佳鹞,自臂之,望见征来,匿怀中;征奏事固久不已,鹞竞死怀中。”
这是广为流传的佳话。“畏卿嗔”是真心是作秀还是真假参半,我也不清楚。但是可以看出,李为了得到魏的忠心,是付出了重大努力的。我感觉魏有点看不上李,李离他的理想型差了十万八千里,就算“作之不止”,也成不了尧舜。李对魏是长期言听计从的,魏却天天恨铁不成钢。君臣关系并不平等,和别的君臣不同,这里是李付出的多。
“文德皇后诞公主,月满,宴群臣于丹霄殿。太宗命公围棋赌,公再拜曰:“臣无可赌之物,不敢烦劳圣躬。”太宗曰:“朕知君有物,不须致辞。”公固言无物堪供进者,太宗曰:“朕知君大有忠正,君若胜,朕与君物;君若不如,莫亏今日。”遂与公棋,才下数十子,太宗曰:“君已胜矣!”赐尚乘马一匹,并金装鞍辔勒,仍赐绢千匹。”
画面感太强。这里李简直韦小宝附身,一副急于讨好魏的样子。魏却一直是这样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状态(嫌弃李不是他心目中的圣君?)。如果长期让领导这样自讨没趣,时间久了领导能不觉得不舒服么。
谓杨师道曰:“卿道姜行本作处,用十车铜,闻谁道?”师道奏曰:“魏徵道。”太宗问公曰:“何以生此?”公不应。太宗再三问,对曰:“道十车铜,是谏争语;臣若道姓名,某即是讪谤,必不益圣德。”太宗曰:“我有事,皆向卿道,今卿乃为在下,不向朕道,是朕尽心向卿,卿不尽心向朕也。
魏传谣,领导问他怎么回事,魏装听不见(我前面有写,这是魏一贯的态度:平常如果李不听他的意见,再和他说话,他就爱搭不理的。这里态度更差,根本不回应了。)领导“再三问”,魏才说是听别人说的,还要给造谣人保密。你是领导你不生气吗?
李说的“我有事,皆向卿道”等语证明了他们君臣关系实际上的不平等,不过是反过来的那种。这里是气极了说的,应该很可信。后来李还愤怒地批评魏“恃宠自骄”,(原文太长不贴了)应该也是心里话。魏后来说出了造谣人的名字,李就不追究此事了。李对他和魏的上下级关系并不自信,还颇有怨言,觉得自己付出的多(毕竟魏的态度实在呵呵)。
无论李世民其他方面有何污点,对房玄龄、李靖等等一帮大臣真是没说的。在他和魏征的关系中,我看是他付出的多。“数引征入卧内”,作秀要跑到卧室里去密谈?至少在李世民眼里,魏征是他亲信。
两人不仅经常密谈,私交看起来也不错。魏征爱酿葡萄酒,李世民还写诗赠给他:“醹醁胜兰生,翠涛过玉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败。”
还有一则趣事能证明李世民在君臣关系上是很用心的:有日退朝,太宗笑谓侍臣曰:此羊鼻公不知遗何好而能动其情?侍臣曰:魏征嗜醋芹,每食之欣然称快,此见其真态也。明日召赐食,有醋芹三杯,公见之欣喜翼然,食未竟而芹已尽。太宗笑曰:卿谓无所好,今朕见之矣。公拜谢曰:君无为故无所好,臣执作从事,独僻此收敛物。太宗默而感之,公退,太宗仰睨而三叹之。
反正在我看来,领导已经做的很好了,这个下属实在傲娇,而且不分场合、动不动就要正颜厉色、一本正经地长篇大论。
最初也许李是要摆姿态、把魏当花瓶,但是最终魏可是长年担任门下省最高长官的。李的诏令,如果他不副署,是没法执行的。他不仅仅可以参与机密,而且可以一票否决。唐初只有三省长官(理论上三省各两人,共六人。门下省侍中应设两人,在魏的任期中,其中六年只有魏一个人)才能参加政事堂会议。他至少是1/6啊,相当于现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领导如果只是为了作秀,让他提提建议也就罢了,不会这样委以重任的。
从唐初的三省六部制执行状况来看,魏的权力是无比大的。三省长官才能参加的政事堂会议,更是在李世民的授意下一步步扩大了权力。政事堂会议不通过的皇帝诏书,都是无效的。如果李对魏只是隐忍不发,还让他当门下省长官、在政事堂参与所有国家大事的决议,让他在眼皮子底下天天晃,这种思维我真心不能理解。“猜忌他就要授予他高官重权,让他参与决定所有机密” 这简直比“爱她就要虐死她”(偶像剧套路)还让人无法理解啊。
于公于私,领导从未亏待过魏征。李对魏就算最开始是作秀,后来肯定不是了,贞观十年之后就更不是了。我认为魏征自己的脾气傲娇、识人不当是酿成推碑事件的主要原因。领导在这段上下属关系中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感情,最后发现下属对他不过尔尔,给他的奏章备份到了史官那里求名,推荐的人还参与谋反,付出和回报完全不成正比,当然气愤难当了。如果真是没有付出只是作秀,李反而会演下去,不会推碑破坏所谓君臣佳话。所以我认为李是付出了精力和感情的,甚至有点一厢情愿;至于魏么,他可能看不上李的操行,我也能理解。
我认为张公子的“爱之深,恨之切”总结的非常到位。李在亲情方面不断遭遇重创,在上下属关系方面反而收获不少,这可能致使他把大部分的感情精力都投入到了他所认为的“君臣之义”这一方面。他写首诗什么的赠给下属是常有的事情。
就像很多在爱情方面付出良多的人,并非如大家所猜测的那样来自和谐美满的家庭,相反,他们和亲戚甚至父母都积怨甚深,常年只对父母负赡养责任而不付出感情、内心深处压抑的感情无法宣泄,所以寄托在了爱情上。
如果读读唐朝初期的史书和一些史料笔记,就会发现李世民对待上下级关系的投入简直有点creepy了,不止是对魏征,这是他一贯的作风。这里面当然有作秀的成分,但有些就明显不是,随便举几个例子:
“它日,食瓜美,辍其半奠焉。尝赐玄龄黄银带,曰:“如晦与公同辅朕,今独见公。”泫然流泪曰:“世傅黄银鬼神畏之。”更取金带,遣玄龄送其家。后忽梦如晦若平生,明日为玄龄言之,敕所御馔往祭。”
有人说吃瓜那里是因为瓜是杜如晦喜欢吃的,李吃着想起了他。能记清楚下属喜好的领导,我见的实在不多。
唐刘餗《隋唐嘉话》载:“梁公夫人至妒,太宗将赐公美人,屡辞不受。帝乃令皇后召夫人,告以媵妾之流,今有常制,且司空年暮,帝欲有所优诏之意。夫人执心不回。帝乃令谓之曰:‘若宁不妒而生,宁妒乃死?’曰:‘妾宁妒而死。’乃遣酌卮酒与之,曰:‘若然,可饮此酖。’一举便尽,无所留难。帝曰:‘我尚畏见,何况于玄龄!’”
用醋冒充毒酒,和下属的老婆撕逼,这简直是莫名其妙。李世民一贯以宽容著称(不论是不是装的),这里却为了管一点下属家无聊的小事,和一介女流之辈怄气,他究竟为上下级关系投入了多少精力啊?
如果你打开《新唐书》,随便看几个大臣的传记,发现全是这种画风,比方房玄龄的:“及渐笃,追赴宫所,乘担舆入殿,将至御座乃下。太宗对之流涕,玄龄亦感咽不能自胜。敕遣名医救疗,尚食每日供御膳。若微得减损,太宗即喜见颜色;如闻增剧,便为改容凄怆。后疾增剧,遂凿苑墙开门,累遣中使候问。上又亲临,握手叙别,悲不自胜。”
比如长孙无忌的:“二十三年,太宗疾笃,引无忌及中书令褚遂良二人受遗令辅政。太宗谓遂良曰:“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是此人力。尔辅政后,勿令谗毁之徒损害无忌。若如此者,尔则非复人臣。”这临死都牵挂着的画风,差点让我以为误入了晋江耽美区。
总之,李其实是有着丰富感情的人。亲情上的屡屡受挫,让他把时间、精力、感情都投入了所谓的“君臣之义”。房、长孙等人陪着李一路走来,李是他们的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老板,同甘共苦几十年,对于李有着深厚的私人感情,也做出了莫大的贡献。至于魏征么,他公司换了好几个,老板更是好几个,作为读书人对公务倒是蛮负责的,对唐王朝也很有感情,然而他对于李的私人付出绝对不如李对他多啊。和房杜、长孙等等不同,魏征不仅没有陪伴他走过艰难阴暗的夺嫡岁月,当时还是他的仇人,而且脾气怪,整天一副大义凛然的臭脸。李在他和魏征的君臣关系上付出了很多,但没得到他所希望的相应的回报,他的幻想破灭了,心里不平衡了,晚年觉得自己亏了。很可能是魏征有点看不上他的操行,觉得他没有达到自己所期望的“尧舜”之类的标准。魏征甚至可能认为李建成比李世民更好,李一想到这些当然不满了。
我每次看唐初的史料,看李的上下级互动,总会产生一种怪怪的感觉。总觉得李对魏简直像是天天买了玫瑰花、早饭追女生的一厢情愿男,因为自身有问题被人看不上,得不到什么积极回应,最终恼羞成怒。李对房呢,简直像房他妈,专业多管闲事,简直处处护短,只要谁涉及到房的利益,他就滥加刑罚。李一生用过两次腰斩:一次是腰斩了密告房玄龄谋反的告密者;一次是腰斩了和房玄龄儿媳高阳公主偷情的僧侣。真正的明君应该是毫无偏私的,李已经算是偏心亲信的典型了。他埋怨魏“恃宠自骄”,难道自己就没有责任?有人告房玄龄,李感情用事,马上断定是“诬告”,连调查也省了。万一房真有问题呢?他和谁私交好,就把谁留到自己身边,加以高官,恨不得天天见;对谁感情一般,就让谁去当地方官。其实在上下级关系上感情用事才是李一生的弱点。有人从玄武门推测出李对于上下级一定是理性甚至冷血的,其实恰恰相反,其实是哭哭啼啼要死要活的。这种类似的画风我还在雍正那里见过,雍正早期和年羹尧的互动大家想必都清楚。我只想说,付出越多,希望越大,失望可能就会越大。魏的推碑事件,可以和年羹尧对比一下,虽然这两件事不是一个级别的。不过因为李偏心的人没有出过太大问题,都算是有能力;他们君臣也算是善始善终吧(表面上);李才误打误撞地成了明君。他和那些理性为重的君主,从表面上看差不多,从对话等细节分析,其实大相径庭。
回复:
嗯,其实他俩理政三观大不相同,简直不是一个次元的。魏和《琅琊榜》中的靖王思路相同,他就不可能认可李的权术。李则复杂得多。魏对于李搞的群臣间的制衡和监督嗤之以鼻。魏曾为房玄龄等人打抱不平。他认为奸佞之徒(他说的御史台官员,相当于现在的纪委)是被李所纵容鼓励,才如此气焰嚣张的。魏认为李的所作所为搞得人心惶惶,让房等人蒙受委屈、担惊受怕。
讽刺的是,和魏征所认为的相反,一般人认为李其实是太过偏袒房等亲信,这是李的污点。如果有人状告房等人的过错,李一般是不闻不问的。魏征自己也享受过这样的偏袒。(“玄龄、魏征、温彦博尝有微过,瑀劾之,而罪竟不问,因此自失。由是罢御史大夫,不复预闻朝政。”)魏征等人并没有被处理,萧瑀反而被罚了。这样的事也不是头一次了。“房玄龄、杜如晦既新用事,疏瑀亲封伦,瑀心不能平,遂上封事论之,而辞旨寥落。太宗以玄龄等功高,由是忤旨,废于家。” 萧瑀因为状告房杜,被“废于家”了,过了一段时间才被重新起用。有人告房玄龄谋反,刚听见这几个字,李就勃然大怒,这个告密者还来不及列举证据,就被李腰斩了。
对于大臣的小过,李并不总是不闻不问,但即使是查问了,比如我前面所提到的魏征传谣一案,魏刚开始不愿说出造谣者的姓名,激怒了李。后来审案官员仅仅是问出了造谣者的姓名,魏认了罪,此事就不了了之了,魏并没有得到任何惩罚。就算事情已经严重到需要正儿八经地讨论该如何惩处了,画风也很可能是这样的:
贞观元年,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尝被召,不解佩刀入东上阁门,出阁门后,监门校尉始觉。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议,以监门校尉不觉,罪当死,无忌误带刀入,徒二年,罚铜二十斤,太宗从之。大理少卿戴胄驳曰:“校尉不觉,无忌带刀入内,同为误耳。夫臣子之于尊极,不得称误,准律云:‘供御汤药、饮食、舟船,误不如法者,皆死。’陛下若录其功,非宪司所决;若当据法,罚铜未为得理。”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何得以无忌国之亲戚,便欲挠法耶?”更令定议。德彝执议如初,太宗将从其议,胄又驳奏曰:“校尉缘无忌以致罪,于法当轻,若论其过误,则为情一也,而生死顿殊,敢以固请。”太宗乃免校尉之死。
依照戴胄的说法,按照律法,皇帝面前带刀这是死罪,误带也是死罪一条。即使李要减轻处罚,也不能轻到这种程度。“徒二年,罚铜二十斤”,“徒二年”是根本就没有执行的,只是说说。这点似乎戴胄都明白得很,他说的是“罚铜未为得理”,根本没提“徒二年”这回事,估计早就料定不会执行。
“罚铜二十斤”这才是真正的处罚,一般是从工资里扣。我粗略算算,二十斤铜也就是五贯的样子吧。现钱在工资形式中不占重要比例,但长孙一个月现钱也有三十几贯吧,再考虑唐朝工资以禄米为主,这样粗粗一算,二十斤铜不过是长孙半天的工资而已。(如果算得不对敬请指出)从死罪轻判成扣半天的工资,李还能道貌岸然故作公正地说出“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何得以无忌国之亲戚,便欲挠法耶?”这样的话,简直是啪啪打脸。林冲带刀误闯白虎堂,罪行比带刀面圣轻多了,结果怎样大家都清楚。他如果听到李这样的话,估计要吐血的。
“尚书右仆射房玄龄、侍中王珪掌内外官考,万纪劾其不平,太宗按状,珪不伏。魏征奏言:“房玄龄等皆大臣,所考有私,万纪在考堂无订正,今而弹发,非诚心为国者。”帝乃置之,然以为不阿贵近,繇是奖礼。”
这次李没有不闻不问,而是调查了,虽然王珪不认为自己有错,事情最后又如往常一样不了了之了。听了魏的话,李并没有继续追究。但是,画风明显不同以往的是,李这次认为状告房等人的御史“不阿贵近”,对他表示了赏识,后面还多有召见。
魏怎么可能认同李?
给事中魏征正色而奏之曰:“权万纪、李仁发并是小人,不识大体,以谮毁为是,告讦为直,凡所弹射,皆非有罪。陛下掩其所短,收其一切,乃骋其奸计,附下罔上,多行无礼,以取强直之名。诬房玄龄,斥退张亮,无所肃厉,徒损圣明。道路之人,皆兴谤议。臣伏度圣心,必不以为谋虑深长,可委以栋梁之任,将以其无所避忌,欲以警厉群臣。若信狎回邪,犹不可以小谋大,群臣素无矫伪,空使臣下离心。以玄龄、亮之徒,犹不可得伸其枉直,其余疏贱,孰能免其欺罔?伏愿陛下留意再思。自驱使二人以来,有一弘益,臣即甘心斧钺,受不忠之罪。陛下纵未能举善以崇德,岂可进奸而自损乎?”太宗欣然纳之,赐徵绢五百匹。其万纪又奸状渐露,仁发亦解黜,万纪贬连州司马。
上面举了几个小例子,说明魏和李不是一个次元的。魏看不上李,从“陛下纵未能举善以崇德,岂可进奸而自损乎?”这句话即可明了。这种句式是不是很熟悉?“就算你考不上清华北大,也不能上这样的垃圾学校吧!”“就算你找不到小张那样的工作,也不能做这样的工作自甘堕落吧!”。这种句式流露出的感情,大家一目了然。
我猜魏所梦寐以求的,是《琅琊榜》里靖王那样的君主吧。他和李,终究不是一路人。
回复凌河与赵照:
这种逾越了君臣界限的特殊关系是一把双刃剑。与大众对李的普遍印象不同,李更像是一个随性的侠客,而非一个理智的领导。在尔虞我诈悲歌一片的封建宫廷,李特殊的上下级关系似乎是一抹光明。然而,这抹光明也埋下了祸患,在李的回护下,李时代的很多高官都明显缺少政治风暴洗礼的经历,他们甚至缺少自保能力,这简直是致命的缺陷。还好不少人都在李之前逝世了。而长孙无忌就没有这样幸运了,他比李活得长,高官一直做到李治时代,结果落得了自尽的下场。
朱厚照是缺少政治风暴的洗礼的代表人物。他的父亲明孝宗和李一样,堪比封建时代的“大奇葩”。这和明孝宗悲戚的童年经历是分不开的。有明孝宗和李这样经历的人,大抵会走上两个极端:一是心理变态,二就是感情过度丰富(不知道这算不算另一种“变态”)。虽然明孝宗的上下级关系没有什么特殊,但是他的夫妻关系却是让人惊叹的:他没有嫔妃,只有一个张皇后;张皇后育有两子一女,一子一女夭折,所以明孝宗只有朱厚照这一个独生子。他们一家三口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过着和平常百姓家一样的生活,这简直是封建时代一抹光明啊!然而,朱厚照一直生活在温情脉脉的父爱中,他哪里知道政治和宫廷的黑暗?明孝宗死后,当了皇帝的朱厚照天天花样作死,最后真的作到死了,连子嗣也没留下。明孝宗绝嗣了。有人认为明孝宗是“优秀的父亲”,有人认为明孝宗是“不合格”的父亲。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评价也可以同时用在李身上,在上下级关系上,他既是优秀的,也是不合格的。
房玄龄足智多谋、能力超群、胸怀广阔、人品近乎完美,可是他的避祸、申辩和自保能力,简直呵呵,他的形象也因此大打折扣。如果真的大祸临头,房这种性格是很难逃过一劫的。大多数宰相经历的来自君王猜忌的种种政治风暴,房没有经历;而且,遇到事情,甚至需要李替他出头(上面已经写了几个例子了)。和众多青史留名的能臣不同,他始终没能在这方面成长起来,这是他最大的缺陷之一。
淮安王神通曰:“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上曰:“义旗初起,叔父虽首唱举兵,盖亦自营脱祸。及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合余烬,叔父望风奔北。玄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国之至亲,朕诚无所爱,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勋臣同赏耳!”诸将乃相谓曰:“陛王至公,虽淮安王尚无所私,吾侪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悦服。
此事就是李替他出头了,并打脸质疑者。以群臣的反应来看,以前不服房的多着呢,李出了头,大家才不敢说什么了。反正我猜想房这时候也说不出什么来,他遇事一贯如此,缺少招架之力。李曾说过:“房玄龄处朕左右二十余年,每见朕谴责余人,颜色无主。”也就是李批评别人,房都要颜色无主(虽然这些人可能是他举荐的,会牵涉到他)。更别提自己摊上什么事了!虽然房是个妻管严、老好人,这很大程度上是他的性格决定的;但是李对他的庇护也是他这方面缺失的重大原因之一。
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宋公萧性狷介,与同寮多不合,尝言于上曰:“房玄龄与中书门下众臣,朋党不忠,执权胶固,陛下不详知,但未反耳。”上曰:“卿言得无太甚!人君选贤才以为股肱心膂,当推诚任之。人不可以求备,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朕虽不能聪明,何至顿迷臧否,乃至于是!”
其实房这样的老好人人缘太好,是被人告发“就差谋反了”的重要原因之一。萧何尚且知道要自污避祸,房在这方面简直是“温室里的花朵”。而且,作为一贯的老好人,他完全有能力拉拢一下刺头儿;他得罪谁不好,非要“疏瑀亲封伦”,团结大多数人,却得罪最爱告人状的人,简直是给自己埋雷。一般人都知道绝对绝对不能得罪刺头儿啊!幸亏李相信并庇护他,不然他的好人缘和好名声早晚害死他。
帝讨辽,玄龄守京师,有男子上急变,玄龄诘状,曰:“我乃告公。”玄龄驿遣追帝,帝视奏已,斩男子。下诏责曰:“公何不自信!”其委任类如此。
我感觉这里房也处理的不恰当,要是我,一定要和这个告我的人一起去见领导,当面对质。这时候房自己应该去不了,但也一定要派自己的亲信跟着去。这基本是人人心知肚明的潜规则。万一领导就相信了此人一星半点的胡说八道了呢?何况这时候是节骨眼上,皇帝要去出征了,留下房统领京师。谁知道这个告状的人能说出什么来?在我看来,房在这方面简直是政治幼稚,而这都是李惯出来的。很多人认为房能当一辈子宰相,一定具有高超的政治智慧,我看不然啊。另外,许多真正有高超智慧的反而死得很惨。
李替房出头是个习惯,他跟别人吐槽魏时提过,“朕昔问房玄龄事,答云‘不知,’徵当即奏称:‘岂有人臣报主得有所隐。”关于房的这一点小破事,有宰相肚量的房都不一定记得,李却一直记在心里,还要替房愤愤不平一下。事实上,只要是关于房的事情,李都极度关注。
司空房玄龄事继母,能以色养,恭谨过人。其母病,请医人至门,必迎拜垂泣。及居丧,尤甚柴毁。太宗命散骑常侍刘洎就加宽譬,遗寝床、粥食、盐菜。
其年,玄龄丁继母忧去职,特敕赐以昭陵葬地。未几,起复本官。
也就是李还要时刻惦记着房瘦没瘦、吃没吃、睡没睡,还要派人排解安慰,送去“寝床、粥食、盐菜”。我猜想一般的皇帝挺多会送去一些普通赏赐,能想到送“寝床、粥食、盐菜”的,简直是亲妈一样的存在。(我这方面不懂。也许是我读书少,少见多怪了,敬请大神指教。)顺便说下,“起复本官”就是“夺情”的意思,张居正夺情的政治风波想必大家都清楚,张居正甚至因此判若两人。不过这里应该没这么多讲究。
.......承乾不敢奏,以告左仆射房玄龄,玄龄以闻.......
说李像房他亲妈,虽然听起来挺荒唐可笑,仔细想想并不荒唐。太子有事,不敢和亲爹说(这时候父子关系还是不错的),要告诉房,由房转告李。谁更像李的亲儿子呢?房和李互相掺和家事,看来是常态。总之,李是时时刻刻记挂庇护着房的,这也是李对亲信一贯的作风。有时候甚至是很荒唐的,比如:
濮州刺史庞相寿,贪浊有闻,追还解任,自陈幕府之旧,太宗深矜之,使人谓之曰:“尔是我旧左右,今取他物,祗应为贫。赐尔绢百匹,即还向任,更莫作罪过。”公进谏曰:“相寿猥滥,远近所知,今以故旧私情,赦其贪浊,更加以厚赏,还令复任。然相寿性识未知愧耻。幕府左右,其数甚多,人皆恃恩私足,使为善者惧。”太宗欣然纳之。
庞相寿算不上是李第一梯队的亲信。他贪污受贿,李还要找借口说这是因为庞他家穷哪,我多赏点东西他就不会贪了。魏怎么可能认同李?从魏的话里,我们也能看出李处理上下级关系一贯的画风。虽然实话说,魏才是李第一梯队的亲信,李记挂他比别人只多不少,比如:
霍王元轨,武德中,初封为吴王。贞观七年,为寿州刺史,属高祖崩,去职,毁瘠过礼。自后常衣布服,示有终身之戚。太宗尝问侍臣曰:“朕子弟孰贤?”侍中魏征对曰:“臣愚暗,不尽知其能,惟吴王数与臣言,臣未尝不自失。”太宗曰:“卿以为前代谁比?”征曰:“经学文雅,亦汉之间、平,至如孝行,乃古之曾、闵也。”由是宠遇弥厚,因令妻征女焉。
魏夸过李元轨,李居然能记得,还让李元轨当了魏的女婿。和魏留给大众的印象不同,魏是李十足的“贵近之臣”,无论魏是否认同李,两人又有何嫌隙,魏是极度了解李的。
唐文皇帝妙于翰墨,尝病“戈”法难精,乃作“戬”字,空其右而命虞永兴填之,以示魏郑公曰:“朕学世南似尽其法。”郑公曰:“天笔所临,万象不能逃其形,非臣下可拟;然惟‘戬’字‘戈’法乃逼真。”太宗惊叹。
也就是李模仿了虞世南的字,又让虞世南代写了半个字,魏居然能看出代写的那半个字“尤其像”,可见他对李的了解程度非同一般。虽然明明了解李,但魏非但没有迎合过李,说话还极其难听。他时时刻刻不分场合的大义凛然一本正经的话先放下不提,他有时候打个“生动形象”的比方,也让人感觉怪怪的。
太宗曰:“朕存心爱养,不愧古人,所未免百姓之言,唯猎一事耳。”时桂阳主在座,奏称:“陛下出游,唯将近亲左右及给使等,何关百姓?”公曰:“譬如人之故旧,有儿子无赖,破其产,虽不关已,然心必恶之。
虽然这事情是魏占理,但是说到李打猎关不关别人的事这个问题,魏非要乱举例子,说就像老朋友“有儿子无赖,破其产”,虽然和别人无关,但是看着心里烦。这个比方怎么看都像是魏拿李和无赖在类比,让人听了浑身不舒服。我们现代人都知道领导面前不要乱打比方,不然有些人难免会多想,但是魏却毫无顾忌。长此以往,李不对他积累怨气才怪。
说到毫无顾忌,长孙无忌才是毫无顾忌呢,这也最终害死了他。长孙无忌去面圣居然能忘了解刀,可见他一贯缺少敏感性。虽然李对这种事情并不在意:
十二年,太宗以诞皇孙,诏宴公卿。帝极欢,谓侍臣曰:“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于是亲解佩刀以赐二人。
“亲解佩刀以赐二人”,这也算潜在危险了。这说明李是毫不在意这些小节的。但李不在意,不代表长孙无忌也可以不在意。长孙无忌习惯了和李相处的模式,新皇帝李治面前他也不知收敛。由于在李的庇护下,他根本没经历过什么太大的政治风波,哪怕是立储风波李也明显偏向了他,所以他空有年龄,根本没成为老司机。
贞观初,仲父太原府君为监察御史,弹侯君集,事连长孙太尉,由是获罪。
凝为监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状,太宗不信之,但黜为姑苏令。
我解释一下,这里是有人弹劾侯君集和长孙无忌一起造反。结果李当然不信,长孙无忌轻轻松松躲过一劫。他可能对这方面缺少敏感度。李治时期,他死在了造反的罪名下。
或有密表称无忌权宠过盛,太宗以表示无忌曰:“朕与卿君臣之间,凡事无疑。若各怀所闻而不言,则君臣之意无以获通。
李的时代有人告他,李居然拿密表给他看!然而到了李治时代,呵呵,李治估计早猜忌他了,他却似乎浑然不觉,最后一败涂地。
在李的时代,李对他可以算是掏心掏肺,比如:癸未,上谓长孙无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为乐,在朕翻成伤感。今君临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欢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负米之恨也。《诗》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奈何以劬劳之日更为宴乐乎!”因泣数行下,左右皆悲。
长此以往,长孙无忌早就失去了对皇权的敏感性和判断能力。在李的时代毫无顾忌也就罢了。李这个人的确毛病不少,也玩弄帝王心术,但是对于亲信,李是只打雷不下雨的。长孙无忌在李时代的日子,其实是“不正常”的。他从这二十几年得出的结论和经验,完全是“温室里”的结论和经验,完全不可以带入到正常的朝代和君臣关系中。如果长孙无忌在李治时期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不至于结局凄凉。
很多人都是经历了一些才成长起来的,甚至经历过多次人生起落、外放贬谪。而长孙等人似乎完全缺少这个经历。如果他误带刀那次,李认认真真给他一个教训,而非罚他半天工资应付给别人看,也许长孙无忌会在这个方面多长几个心眼,也许会在李治朝全身而退。
李似乎是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二十三年,太宗疾笃,引无忌及中书令褚遂良二人受遗令辅政。太宗谓遂良曰:“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是此人力。尔辅政后,勿令谗毁之徒损害无忌。若如此者,尔则非复人臣。”

李是非常了解长孙无忌的,临终前还要特别叮嘱“勿令谗毁之徒损害无忌”,可见他不是不知道长孙无忌平时的言行、处事方式是经常犯忌的。虽然无忌比魏强多了,脾气至少没那么古怪,人也没有特别傲娇。申辩能力比房也好不少,房遇上事就吓得面无人色,人也缺少手腕,毫无还手之力;平时老好人人脉太好,容易犯忌;房还偏偏得罪了最大刺头儿,还不知道修补关系(卫青尚且知道和仇家修补关系)。老领导要时常罩着他们。无忌活到了新领导接任,又身处高位,根本抵不住一轮一轮的政治风波,李的担忧一语成谶。可叹!可悲!可惜!
2/2 首页 上一页 1 2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