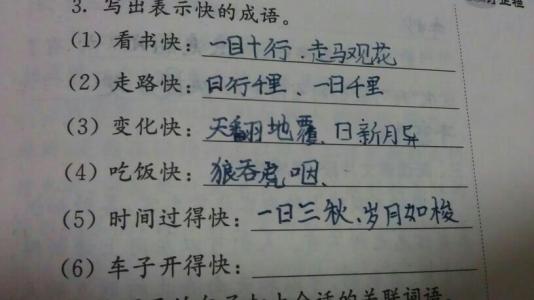1 世界这么大,我看到了,所以要相信梦想。
2 社会很残酷,我知道了,所以得承认现实。
即父母为我大大拓展了世界观的“深度”与“宽度”。今天是我上一周年,回忆一下我的中小学生活。
先说“上山下乡”。我父亲在某中央直属矿山工作,母亲在我出生前也调到了同一座矿山的附属子弟学校,他俩是大型国企的双职工家庭。这种企业的福利一度很好,在80年代这个放任企业滥发钱的时代尤其不错,现代许多人怀念“毛泽东时代工人待遇好”,回忆细究起来,起码有一小半源于80年代的国企生活区。
福利体现在教育方面,就是几千矿区居民独享一个自建的子弟学校,包括初中和小学。学校教师全是科班出身的公立教师(这在那个时代并不容易),有两栋4层教学楼,专门的图书馆、实验室、音乐教室、演出大厅、电化教学装置以及标准足球场。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室内水房,每逢六一,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可以由老师带队去承德(最近的地级市)乃至北京旅游;附属的幼儿园有大型游乐设备,定期会放科教电影。这样的学校,穿越到21世纪初的富庶地区也算很出色;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周围几个农业县乃至整个承德地区的绝大多数中小学都只能说一句望尘莫及。
矿区掠影,几乎所有建筑都和30年前一样,可以想象当时与周边山村的落差。
然后,4年级那年的夏天,就在我策划着怎么用爬山踢球打游戏装满暑假的时候,我父母向我宣布了一个不容更改的决定——下个月你去南台小学读书。以及两条附加规矩:必须和同学一样生活,往返学校不得搭矿区的汽车。(父亲刚刚升任矿山运输处处长)
补充说明一下,我生活的矿山处于燕山深处,周围都是贫困的农村。在建矿山之前,这里甚至连公路都不通,全靠玉米和一点山货过日子。矿区建成后,周围的经济有所改观,但和矿区这个现代工业社会的时代差距也足足有30年以上。平日乘通勤客车往来于县城、地级市和矿区之间,看着晒得黝黑的农民与他们的茅草房、手推车,我虽然年幼也知道这和我生活的矿区是两个世界。听到转学的消息时,我第一反应是——亲生爹娘要把我扔到那个折磨人的地方去?
而且我还没有意识到我要去的学校会带来多大的生活反差。这个小学本来是一个乡的中心校,80年代这个乡撤销了,于是成为另一个乡下属的完全小学,距离乡政府20多里。整个学校只是几排土墙环绕的平房(还不错,都是瓦顶)和一个土篮球场。教室里没有电灯,毕业班的原则是天黑看不见字就下课。全体教师共用一个大办公室,门口挂着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环,上下课时间由教导主任亲自看看手表敲打铁环来决定。这和之前现代化的教学楼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废弃的校园,右边是当年的教师办公室,右侧远方是当年的教室。
一旦到校上学,我发现这个环境并不是看起来那么穷,而是比这还要穷!运动会在河滩上开,木制黑板褪色不说了,居然粉笔也要按课时限量使用,万一用完了,老师要到同事那里去借。同学们从来不会让一张纸只写一面,老师有一辆新自行车算是贵重财产,教室的炉子从来不会把屋子烧暖。学校附属的小商店甚至给每个学生规定了购买额度,要求他们在这里替家庭购买生活用品,给学校积攒一点点批发利润,好到年底给老师发福利——几十块钱的购买下限,每个学生都抱怨高的不像话。
对于这段生活,我在写过几个回答:
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农村的烧柴问题已经缓解多了,但穷困兼生态紧张的地方依然相当依赖植物燃料。这时我爹把我扔到一个山村学校去读书,冬天每个教室每天只有一铁盆煤,不足的部分要靠“砟子”来解决。
秋天,地里的秸秆被割走了,贴地面的一小段秸秆连同玉米根留在土里,用铲子挖一下,连土一起拔出来,形成的块状物就是“砟子”。两个“砟子”拿在手里对撞,把土打掉,留下可烧的部分,这个工作叫“打砟子”。我们有些老师家里的玉米地比较多,就和学校商量好,由学生去老师的地里“打砟子”,得到的烧柴一半归班级,一半送到老师家里。这才保证炉子有燃料。1990年的秋天,下午第六节课就是我固定的“打砟子”时间。
1991年我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来自最偏僻的山村的同学也能做到春秋冬三季有鞋穿,即中国最穷的人也买得起塑料底,至于塑料底冬天易打滑的问题暂且就顾不上了(导热快的缺点可以用用棉鞋垫弥补)。但1991年的夏天,逢下雨,我记得班上还有三分之一男孩和大概十分之一的女孩光脚,即贫穷家庭无力给生长期的孩子配上不同尺码的胶鞋。学校开运动会,田径场设在河滩上,许多男生光脚跑步,脚底的茧子无视砂石的摩擦。绿胶鞋是好东西,一双正经的胶钉双星球鞋是奢侈品,会在几个班之间被借来借去。
值得一提的是,我在校期间,全校师生完成了一个壮举——盖房子。学校要盖新教室,为了节约资金只请了几个大工,再雇拖拉机把材料堆在篮球场上,剩下的工作全靠师生自己出力,而其中学生的工作占主要地位。家里是木工、泥水匠的,跟着大工上房,有力气的高年级学生给他们当辅助,没力气的就用铁桶、挑筐送材料、拌石灰。低年级的孩子每人拿一把镰刀,把小木料清理成光洁的椽子,最不济也要送水送饭,摇旗呐喊。一个月下来,房子居然真的盖起来了。这是我这个土木工程师平生参与的第一个工程,也是我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全学校最好的房子,里有我的一点汗水、有我送上去的灰泥,它真的能教学生做人……
不过,硬件上的差异还不是最大的冲击。和我之前读书的地方相比,这里“软件”的落后更加惊人:
父亲让我到矿区附近的一个农村小学上学,锻炼一下,结果我发现这个学校从农村到老师,通通对外面的世界没有概念。老师鼓励自己的学生努力学习,反复就是一句话:好好学习才能上国中(意味着县办的几所初中而不是乡里的中学),上了国中才能考中专,将来出去工作,不用在这个穷地方过日子!
为什么强调中专呢?因为当地的教师大部分都是文革时期的民办教师,只读过中学,几个优秀的转了公办,还有几个县师范毕业的年轻人,算是接受过现代教育。在他们看来,能让学生摆脱现有生活的唯一方式就是(到县城或者承德市)读中专。至于高中、大学,那离他们的生活太遥远,在他们的头脑里没有概念。老教务主任兼任数学老师,快退休了,人很好,每天勤勤恳恳的工作,但知识水平实在不敢恭维。
有一天,一个读过中专的年轻人请假,自然课没人上,他亲自出马代课。当讲到声音的原理时,书上说真空不能传声,老主任就开始迷惑起来,想了半天之后向大家宣布,以他的看法,真空里也应该可以传点声音,但既然书上这么写了,我们还是要按书上的回答..........可怜的老赵主任辈分很高,我曾亲眼看到他主持村民求雨的仪式,带领年轻人抬着猪肉到泉水前献祭。这听起来恍如回到了上古商周年代,当时知识分子与巫、医还是一回事,然而那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情。那所学校还是中心校,周围许多小学生必须到这里读五、六年级的课程才能小学毕业。我在那里的同学,最终读国中的比例是3.5%。下面的小学情况如何我就不太清楚了。
全方位的落后,结果就是人生观的天壤之别:
90年代初,我在一个纯农业经济的偏僻山村读小学,发现大部分6年级同学都在平静地讨论毕业后的去向。比如说到县城批点小商品去某几个村贩卖,或是学个木匠活。再就是安心回家种玉米,先在同学里号下一个媳妇,叫长辈去说媒是正经………我这个旁听者却一心只考虑能否和初中新同学玩到一起,十年后方觉得当年的谈话令人不寒而栗。
这反映的就是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思考方式的不同。我拥有可预期的少年时代,我的许多农村同学还没有。
初中我就到了县中学读书,从此再也没长期体会过山村的艰苦。但这次浅尝辄止的“上山下乡”,让我从感性到理性理解了中国的底层有多么穷,多么绝望。也让我看到了底层年轻人的活力和梦想。我现在虽然过着京沪双城生活,但我看世界的时候,不会限于一线城市的视角,也不会局限于小资产阶级的社会立场。如果说我的文字还能偶尔体现一点底层关怀和“接地气”,当年父母为我安排的山村历练功不可没。
前面说了,我父母的另一个“出格”教育方式就是频繁地给我请假,从小学到初中,一有机会就带我去看外面的世界。
和当时的邻居比,我家不算富裕,因为舍不得矿工相对较高的薪水,1977年我父亲放弃了高考,到1986年才圆大学梦。家里的细粮大多要支援农村的亲戚,直到1988年左右,j家里还常有以棒子面(玉米)为主食的日子,我为此还和父母吵过架。一直到1999年离开这个矿区,家里始终是分房时配的一套家具放在水泥地面上。但只要有出差的机会,我父母绝不吝惜车票钱,也不怕耽误我上课,常常是父亲下班一句话:“明天跟我去XXX”,我就欢呼雀跃地放下作业打点行装,由我母亲去和她的同事请假。旅行最多学期,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路上。
从我记事起,我父亲先是司机,然后当业务员,到处采购汽车配件,跑矿石市场;我母亲后来调到了组织部,经常要外出调档或培训,两人都经常出差跑上几千里。我要么坐在卡车驾驶室里,要么蜷缩在火车硬座的靠背处,也跟着他们全国奔走,看着整个国家以几十公里的时速在两边掠过。有一年母亲在南方培训,担心我在培训地无聊,还找了桂林的一家小学,让我以外地客人的身份过了一个六一儿童节。我之前也记录过这些经历:
我80年代、90年代,上大学之前经常长途旅行,坐硬座火车或者卡车的驾驶室,在地平线上看到一座座城镇。也不是什么知名的风景区,就是普通的地级市、县级市。每次我都盯着看,觉得很美,非常值得向往。我那时一般随身带着一本80年代版的地图册,前面是地形图,后面是城市地图,城市地图下面还有一些当地风景名胜、特产小吃的介绍。我就盯着几行字的简介,想象地平线上那个影子是什么样,想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去看看。
80年代中期,除了北京上海这两个都市,省会能彻夜点亮路灯的大街大概是纵横各八九条,地级市横竖四五条,县城往往只能用单排路灯连起三四个路口。至于县以下的乡镇村落,到了后半夜几乎是一片漆黑。在农电网络尚不完备、农民家庭全年收入只能买几百度电的年头,没人会为照亮夜空浪费电力。所以,那时候半夜坐火车穿越中国,只要放下窗帘挡住车里的微光,把头钻到窗帘与窗户之间,立刻就能体会到文明的渺小。在时速几十公里的特快列车上,大概隔一两个小时会看到县城的灯火在窗外一掠而过,过上三四个小时,地级市的灯火会照亮窗口几分钟。至于必停的省城大站,算上停车时间,也不过是20分钟就消失的文明岛屿。除此之外,车窗中是无尽的黑暗,黑暗的广阔甚至让你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在地球上。
和夜行列车相比,晚上坐汽车的时候,夜色中多了车灯的光柱。随着光柱扫过,行道树和村落在黑暗中出现又消失,给乘客的感觉是整个宇宙都不真实,如果车后的世界在光柱扫过后湮灭,对车上的人也不会有任何影响。在车辆的颠簸中,就连仪表盘的荧光都让人感到温暖亲切。尤其是冬天,车窗透着寒气,凝视黑暗久了,脚下的暖气是唯一能感受到的文明成果。天气越冷,黑暗越深,你对身边微光中的文明生活就越珍惜。对沿途的灯火就越多一份憧憬和向往。远处寒风中几十盏昏黄的电灯,在想象中可以幻化出无数的温情故事。
那时的旅行并不是现在一般意义上的旅游。我坐硬座车厢,住厂矿招待所,吃食堂,没有导游也没有团友,就是挤在一群成人中看他们忙碌,时而自己溜出去看看城市的日常景象。除非接待单位安排,否则我基本不会去什么景点,也不会品尝什么特色食品。但我依然非常满足,因为我知道我看到了一个同龄人体会不到的世界,我知道这个世界有成千上万的人,过着各种各样的生活,知道我家乡的生活只是无数选择中的一种。虽然我也知道了哪里谋生都不容易,知道大城市的繁华不会凭空让我享用,但少年的乐观让我坚信,走向那个大世界一定意味着更精彩的生活。当年“接班”盛行的时候,很多同学会谈论自己将来如何在这个矿山小镇谋个舒适职位,我嘴上不反驳,心里却暗暗下决心:我的未来一定属于外面那个天地。当然,我也能理解他们的想法。
80-90年代的学生,即便生活在讯息发达的城市,往往也很少有机会离开自己的家乡,最多去一趟省城,就能成为几年的谈资。唯独我能用自己的感官体会一个纵横几千公里的国家。在高考之前,我已经去过十几个省市,见过大城市的灯火,吃过岭南的水果,见过大海无边无际,也知道远方同样有贫困的街区和乡村。今天的旅行者可以坐飞机高铁,几个小时就掠过我当时一星期的旅程,但这是点到点的交通方式,他们看不到我在尘土飞扬的路上体会到的那个国家。从这个角度说,那个中国比今天游客眼中的国家更大、更具体,我甚至很难给我的儿子复制类似的旅行体验。
父母提供的旅行机会,让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就确信,生活必须和整个社会联系起来才能真正精彩。我以孩子的视角看到的那个普通人构成的大社会,至今也是我理解这个国家的重要资本。刚才我翻了翻过去一年的回答记录,发现大多数回答和我的日常生活并不相关,甚至未必会提高我的薪水,但我依然可以从获取、分享这些知识中获得乐趣,这就是我对眼前的生活最满意的地方。总之,感谢我的父母,感谢他们把我的心培养的如此之“野”。
1986年,母子合影
我这一年上,对两个简短的答案印象深刻:
有时候,看不见贫穷的角落也是没见过世面的一种。
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
现在回想一下,这和我父母当年的家教很是契合,他们只是没把自己的的教育原则写出来而已。如果他们当年有可用,“世界这么大,你应该去看看”之类话或许早就流传开了。当然,不是每个家庭都有我父母的机会,但那个年代还是有很多人努力向子女、学生介绍了外面的世界,,展示了现实生活的复杂。我妻子的小学语文老师教到《我爱故乡的杨梅》一课时,专门去店里买了杨梅罐头,让每个学生体会一下这来自遥远江南的酸甜味道,相信她的努力在今天也会有百倍的收效。
上一周年,29万个赞,绝大多数要归功于父母、老师当年恰当的教育上一周年,29万个赞,绝大多数要归功于父母、老师当年恰当的教育
相关话题:
2/2 首页 上一页 1 2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