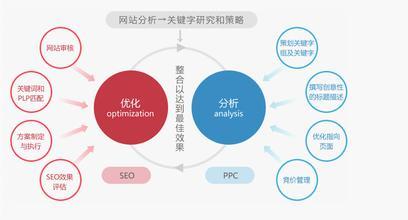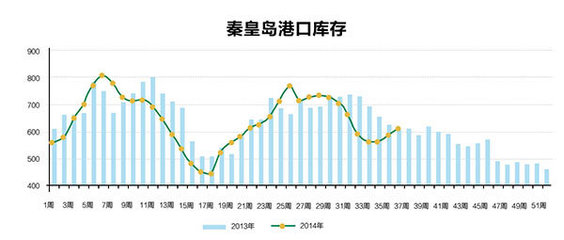06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看完就立刻回到生我养我的热土,这里有我的家;
16年,春节没回去,今早妈妈说,没火车票了,村里到上海打工的队伍要租车过来;
昨晚看纪录片《Home》,这样一个体会:三百年来,百分之三十的人参与工业化,产生的价值被百分之三的人撸走。我们以为,世界的矛盾就在这百分之三和百分之三十之间,而那百分之七十呢?没人知道。
世界人口总量的三分之二从事着农业劳动,而我们日常的粮食消费仅仅依靠百分之三拥有现代农业技术的农民就可获得,那三分之二从事农业生产的人,除了生存还能追求什么?可想而知。
你能想像全球还有三分之一的人,他们的生活中完全没有机械,一切可以依靠的力气都来自于自己的双臂吗?你能想象当下这个世界只有百分之三的农民用上了拖拉机吗?你能想像自己每天上班安步当车吗?我觉得你不能。
(不要问我为什么这么多三,可能纪录片导演喜欢这个数字?而事实上也差不离。)
看到有人在网上问,如果没有电,人类还能生存吗?这个星球还有十亿以上的人生活在无电区,你知道吗?
好了,不扯远的了,扯这一堆,没有一点干货,只是想和大家一起去看看更大的世界,那些除了媒体上会出现的百分之三十三之外的人生。
下面聊聊2016年中国农村的小民生活。
可能有人会说,你说的那些和我看到的农村完全没关系啊,我们村子眼看高楼起,小车开,一片欣欣向荣啊!是的,你看到的,我也看到了。从00年记事儿开始,我看着每个家庭从铁锅到铝锅再到电饭锅,看着17寸黑白电视到29寸大头彩电再到现在的液晶电视(这个村里只有十几台吧),看着村里开始装电话到开始有了第一部诺基亚到现在几乎每个大妈都有智能手机,我还看着洗衣机从一开始只有一台到现在有一半的家庭都有了(这个真多亏了家电下乡宣传的好),还有电脑的从无到有,从有到现在的十几台,嗯,我还看着村里从只有一家砖瓦房到现在的绝大部分都住在了钢筋水泥的房子。
我无意抹杀农村这些年的改变,而且这些改变让我欢欣鼓舞,但是吹捧农村如何好我却绝对不能赞同,如果没有家家户户年轻劳力在外面的工厂一天十二个小时的死拼硬干,我们的农村又会是什么样子呢?看着一屋子家电舍不得电费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应该有人理解吧?
我想自己之所以被邀请回答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之前的一个答案:,很多朋友私信给我,怎么会有这么惨淡的人生,甚至还有人问这么偏远的山区到底在哪里,可不可以去扶贫或者做调查?我看后只能笑笑,你们以为回答中的贫困是被我妖魔化了,我能理解。毕竟万丈高楼平地起也是我们农民子弟无法想象的。上海满大街的咖啡馆,家家户户摆放的花瓶和红酒,随处可见的自动售租书机,场场爆满的讲座、电影和歌剧……别说农村人无法想象了,就是一般地级市的你,能想象吗?
两千年驯化出来的种子,在近二百年内,绝大多数不再种植,人类进入农业文明两千年来最好的时代,却在工业文明面前不堪一击。但这一切,迅猛而来的现代工业文明的一切,与全球百分之七十的人口基本无关。
但是,走进城市的农民子弟集体失语了,大家努力摆脱着自己身上的乡野气息,学着享受都市生活,我们看不到凤凰男女对城市的惊叹,只能看到城市的王子公主们对农村的同情与不耻。我爱人问我,就在中国,就在我们身边,这么多的人口涌入城市,这么宏大的一幅历史画卷,为什么当代文学没人写?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用着八十年代的《平凡的世界》来表达自己对城市的向往与恐惧?
然而,我们就是不敢提及,说城市好,家乡的父母还处于传统观念,怕你忘了本,免不了骂上一句“五谷杂粮吃出你南腔北调”,说城市不好,身体却很诚实,不断往城里挤。索性,偷偷攀岩摸索,一切的酸甜苦辣,自己尝试。
和母亲通电话,我说,上海是另一个世界,和我们的世界完全不一样。我感觉到了电话那头的母亲怔了一下,是啊,那一方温情的热土,可能就要在我这一代变成一片荒芜,她高兴,也害怕。
前几天,一个姐姐像发现什么大新闻似的告诉我,一个参加冬令营的姑娘已经五天没洗澡了,我只能笑笑,除了985,211院校,我国那么多院校,有多少宿舍内配了卫生间?反正我上学的时候,不足二十平的宿舍住八个女孩子,洗澡有洗澡卡,一次六块钱,当时我们寝室有姑娘一个月的生活费不足三百块,如果每天洗澡,且不说天寒地冻湿漉漉跑回宿舍,单这洗澡一项的开支,就得花光生活费了。
但没有人告诉别人自己是每月洗一次,相反,我在北方没有暖气的民租房里,看到年轻的姑娘们跺着脚忍着冷擦洗着身子,然后在第二天的工作场合有意无意间嘲笑着不穿睡衣睡觉的阿姨。
生活水平的上升往往伴随着无数的笑话,这些正在上升的人对原地不动的人的笑,以及,这些正在努力改变的人,被其他所有人当滑稽小丑的笑。
背离了自己曾经的生活,还不忘踹上那些曾经一起生活的人一脚,转过身想拉住上流人的衣襟,别人又嫌弃你脏。
整个社会就这么拧巴着,大家只能偷偷改造自己,改造生活。
物质上向往城市的农村,精神上却很排斥,不是不向往,只是感受到了来自城市的敌对和鄙夷。
好吧,说多了太醉,写个对门邻居的亲身故事好了。
那年村里来了个外乡女人,村里有三户光棍,随便谁家拾掇了都是好事儿。女人在老赵家住了一晚,老赵家把人赶出来了,赵老头传出话来说是“石女子”,老赵家四条光棍得找个能生育的女子,这个不能要!女人又被拉在安哥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去看的邻居装了一屋子,我也去了,安哥和我家就隔一个猪圈的距离,平时很少去,每到杏子熟了,我们这群娃娃才去他院里,光棍的家毕竟凄凉些,不好玩。魁梧的安哥坐在柴火旮旯添着火,其实安哥挺实在的,他妈走得早,没人张罗就给耽搁了。那女人坐在炕上围着被子,一条腿赤条条露在外面,模样我倒是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大家有一搭没一搭聊了半天抽烟的问题便走了,安哥给女人买了包瓜子打发去了,说是“不够数”。多年以后,我总想起一个头发凌乱的女子,歪着头嗑着瓜子儿在对着我笑。
两家忙活完了,根子说,这女人他要了。根子是谁我并不知道,虽然我们村只有七十来户人家。日子过了大半年,根子跑我家来了,他女人想回娘家没钱,他家院子里有三颗大槐树给我家勾三年槐花,他先在这儿支一千块钱,我爸在矿上上班,家里有些闲钱自然愿意帮这个忙,我也就第一次去根子家,第一次见了根子妠妠,妠就是妈,我们那儿叫换妈的人现在都没过五十的。
他家院子挺整齐,槐树上掉下来的东西也都扫的一堆堆儿的,我刚进院子,根子妈就踉跄奔过来了,我吓得直往我妈怀里钻,根子拉住了他妈,对我们笑笑,说他妈就喜欢小孩儿。我爸拿着锯子上了树,高大的槐树是没有叉的,让人看着担惊受怕,大枝大枝的树被我爸锯下来,根子和他妈站在边上就那么看着,我爸干活糙,结果就是后头两年这几棵树再没生什么槐米,三年完了,根子就把它们锯了。
差不多一个来月,去我家串门的老太太们就开始议论外地女人靠不住,跑了。再过了两年,我家的新房建成了,位置选来选去还是选在了根子家对面,他妈还是那样,头发编成两个大辫子,用草或者不知哪里来的布绳子扎起来,整天在荒草地里穿来梭去。这会儿我也见她多了,不怕了。她常站在远处看我家小卖部里的东西,我也常找她说话,每次说不了几句她就害羞要跑,她喜欢自言自语,我有几次跟在她后面仔细听,“公社打了那多菜盒子,不给我吃,公社那多媳妇子吃菜盒子,不给我吃……”听多了,老是那几句。本来想给她梳下头发的,根子妈不配合,我也没趣了。
那天弟弟从外面跑回来讲根子家好多人在看碟,电视演的一个女人被三个男的脱光了打,串门的大婶子骂道,这群不正经又在看黄碟了。弟弟很认真地嚷了起来“那碟是黑颜色的”,惹笑了一屋子人。
成了邻居,我也从没去过他们家里,我不知他们家吃什么也不知他家谁做饭,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根子经常梳着中分,瞪着一双锃亮的皮鞋,还有他妈满身的野草,再有就是死了。
根子毫无预兆就死了,那天雪下得很厚,我平时早自习下了在学校吃饭,那天想踩雪就跑回家了,吃完饭妈妈出来送我,有个闲汉在外头喊根子,我妈就奇怪了,平时下雪天根子早早就会出来扫雪的啊。反正不碍我什么事儿就那么走了。
中午回去,门外头聚着一堆人讨论着舌头伸了多长,根子家门上挂着黄纸白纸剪的帘子,很久来他家一次的姐姐铛儿也在,黑瘦黑瘦的,给人递烟的时候显得越小了。
根子死了,用的是他的裤腰带,根子死了,没有吹打,没有棺材,没有哭声,根子死了,三天后村民帮忙把他住的那孔窑封住,那里成了他永久的穴。
根子死了,他妈还活着,深入简出,话也少了,又一次跑我家来给我送了一个泥馍馍。
我妈说她在家看电视,突然听到几声狼嚎的声音,腿都软了,趴在窗户上看,根子妈站在她家窑顶上。
没几天,根子妈就死了,死因不知,葬地不详。
又是一个秋天,风已经有点冷了,各种秋虫的叫声凄厉厉的,说根子埋在家里太臭的邻居都也不再念叨了。我九点放学,爸妈不知去哪儿还没回来,小姨和弟弟在家,门锁的死死的,小姨让我从窗户里进来,说外面有个人一直沿着我家墙根走,发出一些怪声,我们三个把电视声音开老大,还是能听见那唉咳声,声音持续了几个晚上,邻居都说是根子他弟弟怀子回来了,我从来不知道还有怀子,过了几天终于恢复了平静,怀子被他姐送去远处当小工了,再也没回来了。
嗯,农业社会的普通人生罢了。毕竟今早已经看到了村民匆匆背起行囊出来闯荡,希望总会有的。
不要再说什么不舍的乡愁,勇敢的往前走。成为被剥削的百分之三十,与不被剥削的百分之七十,不可同日而语。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