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017万和8900多万 谁才是贫困户?
“精准扶贫”,就要先找到到底帮谁。谁才是贫困户?这估计就够的“精英”们忙得外焦里嫩了(我觉得要解释清楚我也外焦里嫩了)。
不细想的话,这好像是个理所当然的问题。但光这个,就 把某省的第一书记们折腾了好几个月,到现在还没消停。
中央文件和法定数据:
1.“精准识别”是指:“通过申请评议、公示公告、抽检核查、信息录入等步骤,将贫困户和贫困村有效识别出来,并建档立卡。”(2014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到目前为止,根据“建档立卡”(这项工作现在仍在进行),得到的全国贫困人口数字是8900万。
建档立卡其实就是民主评议加多维度考察贫困。比如这个村有10个贫困户的名额,那就全村开大会评出最穷的10户,具体看的指标包括收入、支出、住房、农田、家里病人和学生的情况等。(实际操作中,名额不是按户给的,比这更复杂。)
2.2014年底,我国的全部贫困人口是7017万,比2013年减少了1232万。(2015年2月发布的《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法定数据,贫困人口数是7017万。
这个 数字是在全国7.4万的抽样样本中推测出来的。我一度觉得这不太靠谱吧,问了人大农发院的一个教授,他解释说这还是很靠谱的,随机抽样,样本量够,执行规范的话,可以推测总体。国家统计局在全国每个县都有调查队,统计贫困人口的唯一指标是人均纯收入(低于2736元)。这涉及到支出和收入调查,调查队采取记账的做法,每有一笔就记一笔,是个需要长期观察的繁琐工作,基层的非专业人员做不来。
然后这两个数字之间的错综复杂的联系是,建档立卡的统计规模依据于统计局的法定数字,不能超过后者太多。但其实这种依据十分“不精确”(仅是我在B县看到的情况,别的地方不知道):
去年8月份,当“建档立卡”的通知一层层从中央、到省、市州、再到我去的B县Z乡乡长手里的时候变成了这样——
领导上午打来一个电话:你们统计下你们乡各行政村的贫困户是谁,统计的规模依据是“×××”——这个 数字就是国家统计局之前公布的2013年底的全国贫困人口数,也就是7017+1232=8249万人加上减贫指标,层层分解到各县、乡、村的人数。
领导说了:“晚上你就得给我报来啊。”
然后Z乡的乡长和全县各乡乡长就开始加班,给村里打电话,据说当晚B县各乡的办公楼是一片灯火通明。
当天接到通知的村支书、村长们,显然并没有时 间和精力“申请评议、公示公告、抽检核查”。报贫困户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于是村长们仍然按照惯例写了自己、自己的亲戚和熟人为贫困户。倒不是贪钱,因为按照惯例,这个钱也不是发到户里的,而是直接发到村上,有的村就全村分了,有的留着修路、修水池什么的。于是这个其实十分“不精准”的数据就被报上去了。
到今年6月份,习大大去贵州考察了一圈,大谈精准扶贫。广西某县出了篓子,因为评上贫困户的居然有车有房,上面就怒了。
习大大说话比国务院管用不是一星半点,大家这才理解“精准扶贫”、“精准识别”是来真的!于是各省就开始前所未有的严格核查到底谁是“贫困户”。
要命的是,对B县的各乡来说,去年8月报上去的那个数据现在成了他们的镣铐。上面的指令变了几次,开始是说,得把不是最穷的踢出去,但户数不能变。这样重新整了一遍,因为具体哪户已经不一样了,而每户人口又有差异,最后这个人口数就差别很多。
那上面又说,你们人口不能变,户数可以调整。于是这就变成数字play了,既得是最穷的,人数又得不多不少差不多占上(可以适量少,别多),然后户数又得凑成整的(最后帮扶政策是按户来的)。比如这个村的名额是90人,现在还剩5个名额,有3个家庭差不多穷,那谁能幸运地变成贫困户,就看谁家刚好5个人,不成的话,4个也行吧,反正您家要是有6个那就没戏了。
由于方法不同,国家统计局的法定数字是单纯考虑收入,从抽样调查中推测出来的7017万人。而建档立卡通过开会和实地评测(其上限的依据是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按照建档立卡工作的细致要求,可以在法定数据上上浮10%,个别困难省份可以上浮更多,文件太长,就不粘贴了)找到的是8900万人。这两个数据单看数字就差了1900万,具体到里面涉及的人群,差别就更大了。
所以2020年要全部脱贫,是7017万还是8900万?国务院扶贫办的副主任洪天云在某次发布会上很模糊地说:两边都 要脱贫。这意味着,其实我国要脱贫的人口既不是7017万,也不是8900万,可能总规模达到1亿多。
那位人大教授的说法是,建档立卡的还好说,因为“精准扶贫”能覆盖到,而在某些落后地区,那些人均收入很低,但由于名额有限无法被纳入贫困户的人就比较难了,只能靠“地区经济发展”带动了。
在B县的C乡,我去了一个非贫困村的非贫困户家里。全家有5个老人,3个小孩,只有1个女性壮年劳动力,5个老人里3个有残疾:瘫痪、智障、聋哑。我去的时候,瘫痪的那个老太太就在门口一个小棚子下,自己晒太阳,海拔3500米以上,自己在那吹风。就这种家庭都没评上贫困户,据说村里有更困难的。
这个村也没评上贫困村,乡里有5个行政村,2个贫困村名额。
这个非贫困村的贫困发生率(贫困人口除以总人口)是11.7%,另一个该乡的贫困村的贫困发生率是12%,0.3%的胜利!
目前省里刚出了一个文件,说精准扶贫工作中,贫困发生率低于4%的村可以申请“脱帽”贫困村。但人远远高于4%的村却想戴帽而不得。而且按照 惯常的行事法则,脱帽是可以的,戴帽是万万不可的,除非重大灾难,要不你怎么解释国家做了这么多工作,你还返贫?基层也不愿意承认。
那些贫困发生率本来就甩了4%几条街的村就只能自求多福,期盼“地区经济发展了”。当然也不是毫无指望。因为全县的贫困发生率也得低于4%,才能申请脱帽贫困县,所以这些非贫困村理论上不会被抛弃。具体在扶贫政策的倾斜中如何平衡就看基层智慧了。
----------------
地区经济能发展吗?
某第一书记(从省、县一级派到村里的,专门负责精准扶贫的驻村干部)的原话:党觉得他们穷,他们自己没觉得自己穷啊!
这是第一个难点。刚去的第一感觉可能是村民很懒。问养不养×,不养。问种不种×, 地不够。问 去不去打工×,语言不通,家里老人小孩走不开。
总之,虽然你看人很困难,人自己似乎并没有强烈地脱贫愿望。
但要钱似乎是很有经验的,县里让某村种车厘子,免费提供树苗、技术,村民就说了那要一亩给1300的补助。
后来有一天,车沿着金沙江东岸的公路,先后经过了一片荒芜的核桃林、葡萄架子后,第一书记就又感叹了:其实也不是懒,我能理解,以前也让人干这干那,也没实际效果。
这是一个信任问题,那些被评上贫困村的,一般都是长期扶贫没什么效果的,村民已经不信你政府能帮我怎样怎样了。估计以前也“忽悠”大家发展过不少产业,都不了了之。最重要的,好多村里的路都没修通。那村民的想法就很实际,他们不看长远利益,能拿到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村子发展的另一个障碍是,有些村的基层组织太弱了。比如村支书是常年找不到人的,村长没什么威信。那这种村很难发展集体经济,要搞合作社、要一起组织去路边卖卖水果,都很难。
然后抛开以上,最大的障碍是,有的“地区”,我真是觉得就不适合发展经济。比如C乡,5个村都在海拔3000米以上,干旱山地,除了那种雾蒙蒙一团的荆棘丛和石头,就没有别的东西。有限的劳动力,种点地已经很难了,很难搞什么增收的产业。
针对这部分人,在扶贫政策“五个一批”中,有一条是“搬迁扶贫”。但搬迁扶贫首先是又有名额限制的,在困难地区,这个名额不见得够。另外 每户的经费只有20000,从政府角度来说,考虑到总量,是不小的投入,但对每户来说,如果他们搬到别的地方没有新的生计,那20000也没多大用,盖个房子都不够,脱贫还是很难。
除了这些偏远的乡,B县的整个问题是离中心城市太远了,到省会要开15-20个小时的车(看大车还是小车),离最近的 高速公路有900公里。这样什么东西都不好运出去,市场是十分有限。
从省会来这里的第一书记呆了几个月之后,画风变成了:到××才5小时,那很快啊。到××才7小时,那很近。我开车带你去××,一天就能到。
比较神奇的,在这个十分偏远的县,现在居然有两个大学生创业项目。数十年来绝无仅有,好歹解决了当地几名青年的就业问题。 但项目能不能坚持下去,就有很多因素了,在北上广的都嚷着“创业维艰”了。
------------------
民族地区的特殊问题
1.语言。30岁以上的农民,会说汉语的很少。汉族干部去村里一定要带翻译的,要不和人 无法沟通。当然带了翻译也有隔阂,毕竟语言不通。然后语言不通也导致 村民不去内地打工,觉得去了会受人欺负。以前援建B县的S县,组织了一批当地居民去S县工厂,结果后来工厂说:你们别来了,工资照发行吗? 据说这批人经常工作着工作着就翘班不见了。语言不通还会直接“致贫”,比如家里有人生大病,得去内地求医,就必须带个会汉语的向导,或者去了内地找个导医,要不无法和医生沟通,这就得多花一笔钱,保险还不报销。
2.宗教信仰,会影响到一些特定的行为。比如当地的藏族居民普遍比较抵触养鸡合作社,因为他们觉得杀生不详。养猪、牛顶多一年杀一两头,养鸡就得杀很多只。
3.长期的补贴政策导致的“等靠要”思想。就是拿钱已经拿习惯了,产业反正从来没发展起来,所以还是希望等着拿钱,这个多轻松。
----------------
教育真的在发展
这次去之前,我对藏文化的感情和认识大概是必须保护文化多样性啊,这个现在没变。
但有一个很无奈的事实是,在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同时,我越来越觉得孩子还是得学好汉语,这是很实际的生存问题。但现代化的、全国性的教育必然又和保持传统文化和本地文化有一定抵触,别否定这一点,毕竟大家的学习精力有限。
前几天看到汪晖在一篇文章里说:
“比如新疆的语言,那里的青年语言能力并不弱,他们会很多种语言,但都没有用,只有会说普通话和英文才能找到好的工作,才有能力,他们会的那些多种语言因为不能在商品市场上进行交换。换言之,能力只有变成商品才能被计算为能力。”
他对这种“能力平等”是持反思态度的,但怎么办呢?反正现在也只有学。
在下一代中,教育水平已大大提升。周末我去当地的寺庙里,刚好那几天在念长经,远近乡里都来了,中午休息的时候,很多小孩子在寺庙各个角落拍板。我看了看,卡片有两大流派:植物大战僵尸和熊出没。
才上小学1 、2 年级的学生,字认得很多,“僵尸”也认得。我在那发微信跟人感叹这事,他们还能跟着念。
去村里,如果碰到已经上小学的,可以抓来做翻译。相比他们30+的父辈,小孩子反而更好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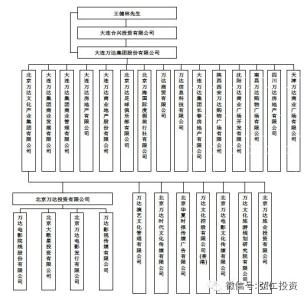
中学生就更厉害了。念长经的第一天,特别有趣,隔了两条街,寺庙在讲经,这边县政府附近, 共青团在搞一个活动,来了很多中学生。活动本来要绕城一圈,但寺庙那边法事活动的时候历来是要交通管制的,于是就看不到举着团旗和横幅的少年们走过寺庙的场景了。(这个能有拍下来是很好 玩的素材。)
活动结束了我和高中女生们聊,真是爱笑的活泼的女孩子们。而且说话出乎意料地正能量又真诚, 真诚地让我惭愧。印象比较深的有:
“读书,找了工作做父母的后盾。”(我到现在还没这个觉悟和行动力)
“我哥哥去年17岁就嫁了(这边挺多倒插门的),家里读书好的才能读到高中。”(这是一个女孩子说的,看来这里不怎么重男轻女)
“我们老师对我们可好了,有这么好的人啊!早自习晚自习都陪着我们。”(回想一下,我们高中老师也是早晚自习都“陪着”我们, 然而……)
这群孩子感叹能上到高中很幸运。我问她们还去寺院吗?她们说上学后就太忙了,现在一年去一两次的样子。(全住读,而且在B县,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周一到周六上学,初中开始有晚自习,大概孩子放假了家长也不好管。)
在B县的初中,有援建单位的援藏老师。按照省里的规定,教师要评中高级职称,都要去援藏。援藏的老师对当地师资力量是极大的补充。
某天早上10点多课间,我去初中找援藏老师班上的中学生。他们说最大的改变是语文变好了,汉语对他们跟外语差不多,援藏的这位老师来之前,他现在带的两个班90多个学生,只有5个人及格,现在基本上都能及格。
不管是高中校园还是初中校园,都有一个除了国旗、国徽、藏文发明者“吞弥桑布扎”之外照耀校园的异类——韩流明星EXO和权志龙。
权志龙无敌!我有天去某贫困村,在某家的家具上也看到了权志龙,他旁边的贴画是TFboys里的王俊凯。
一位来自西藏的师兄评论:本质上是全球化、现代化。
我比较同意。“汉化”这词的问题不是不和谐,而是不准确。
中央的一个提法是“扶贫先扶智”,听着挺口号,我觉得说得挺对。
藏传佛教寺庙,传统上,在藏地其实有学校的 职能,培养政治家、艺术家、文职人员、法律人才和医生。但是这套体系,现在真的是越来越松散崩溃了,这不仅是汉化的问题,这是一个宗教逐渐被世俗取代和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的过程。如果说临公路的藏房上插着的国旗,多少有点刻意装门面的意思;那走在县城里,GAP、耐克等国际品牌的Logo,粤语流行歌曲,辛普森一家的印花T恤,则是无意识地成为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高中生、中学生大多都有QQ,10年过去,那只企鹅依然是少男少女的最爱。但10年过去,今日的少男少女们已经很少去寺院了。
-----------------
水电站,磕长头去拉萨的人
去C乡的路上,路过金沙江上正在修建的一个水电站。水电站建在S乡, 这个乡一片欣欣向荣。
水电站会淹掉一部人房屋和田地,据说每户的补贴可以达到百万级别。
水电站带来了3万多工人。我到的时候,S乡有茶楼 宾馆 KTV 夜宵铁板烧什么的,今年新建了很多商店。
再过一个多小时,颠到了C乡,整个乡中心就几栋房子,政府和小学用的一个院子,和S乡根本就不像平级的行政单位。
一个水电站,彻底拉开了两个乡的距离。当村民们高兴的时候,一个他们可能目前不很在意的问题是水电站的环境隐患。
当然,水电站的环境隐患到不见到就是S乡的患了,上下游指不定哪儿,这个项目具体的环境审查不清楚,不是采访主题。据说C乡也要建水电站了,工程已经批了,还没正式开始。
也是在去C乡的路上,一段人迹罕至的公路上,碰到4个磕长头去拉萨的人。大冬天的,但是农闲,所以藏族农民选这个时间去朝圣,估计磕去得3个月,2016年了。
两年前去拉萨的时候,在布达拉宫,成群结队的围着布达拉宫磕头的人让我震撼,让我赞叹这种文化的惊人的美感。
其实现在想想是“异域风情”,被一种我不了解的信仰的神秘所吸引。政治不正确一点,信仰和愚昧一线之差。
路上的这4个人,拉碴的胡须,打结的头发,灰扑扑的外套,脸上依然杨怡着那种相信者的幸福。我却忍不住毫无浪漫地想,这几个算贫困人口吗?这样的藏区农民,一生无灾无病就罢了,万一摊上几个上学的小孩,摊上一个病人,分分钟穷到没有朋友。
巨大的现代机械、繁忙的工地、商店、水电站; 寂寥公路上的几个寂寥的磕长头的人。无论借助哪一种方式, 人世的福祸总是难以预测。
几百年来,C乡的乡民进山、出山的时候,都要去“阿翁苍空”(音,意思是爷爷念经的地方)敲三下,供奉一笔香火。这是一块传说中有灵性的石头, 人们求它保佑出入平安。现在石头上建了一座小小的房子,两个喇嘛在此修行,公路就在房子边,
这一段水泥路过后,颠簸不平的石子土路盘山而上,C乡在更高远处。
--------------------
第一书记们在干嘛?第一书记的老大是谁?贫困县和贫困县也是不同的
最后,和B县无关,说说本省的整体情况。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贫困县和贫困县是不同的,第一书记和第一书记也是不同的。
本省的做法是把××个贫困县分给省级领导和省直厅级单位,然后从这个县里选一个贫困村包村(该贫困县的别的贫困村的第一书记由市级或县级单位派驻)。
省级领导包括省委书记、省长、纪委书记等等等。当然这么大的领导不可能跑到村里去做“第一书记”,那么他们就派自己的手下,比如秘书去下面做具体工作。
然后省直单位,就多了,包括妇联、团委这样的群团组织,包括广电 局、知识产权局这种你也不知道他们去了村里能从哪里入手的单位,甚至还包括大学(和有些机构相比,大学可能算资源多了)。
省级领导的资源最多,他们的工作组到哪里扶贫, 可能就有国企、公司各种资源贴上来。而一些比较尴尬的单位,比如妇联,我没具体了解过,实在想不出他们该如何“结合自身优势”来搞扶贫工作。
这××个贫困县的情况也是各不相同的,有的区位条件好,交通相对方便。有的则十分偏远,一时难以脱贫。省委书记会挑哪种?省长呢?纪委书记呢?大家自己想吧。
不管7017万,还是8900万,到2020年,要全面小康,就必须完成精准扶贫。其实只有4年了。一个婴儿学会说话,一个大学生毕业,就是这么长时间。
转眼到了年底,上一年的“精准核实”刚做完,“精准减贫”的指标就下来了。不出意外的话,在2016年 初,国家统计局即将发布的《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我国的贫困人口就会变成6000万左右,又减少了1000万!数据发布的之前之后,又有多少个村长、乡长得开始新一轮的数学 play?
我去的几个乡,基层工作人员都是连轴转的模式。有一个小伙子去走访贫困户,说到那家有个什么病人还是怎么(他们中间在说藏语,我没听全)。他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我左下腹疼是不是阑尾炎。他说他疼了两天了,没请上假看病。我说右边才是阑尾。他说自己管得太多了,又管防火,又管防汛,又管退耕还林……另一个乡,本来有个今年要结婚的,因为没请上假, 婚也没结,这不是边防战士的标准故事吗?
但他们已经这么累了,工作也没什么起色,效果今年还看不出,精准核实才刚刚收尾。
和扶贫工作比起来,“创业维艰”什么的, 哎,算什么呀。 2/2 首页 上一页 1 2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