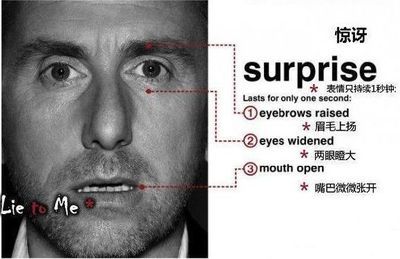1.亨利希玻尔《爱尔兰日记》
Heinrich Böll: Irisches Tagebuch
坐标:爱尔兰。
“在爱尔兰,水是硬的。”
如此开篇。这一概念也贯穿这本薄薄旅行日记的始终。
德国人素来推崇爱尔兰。不论是爱尔兰所占据的地理位置,爱尔兰这个民族,还是以其高产出的文学大师为代表的现当代爱尔兰文化。
这种推崇自然与译介相关。有各种形式的译介,可以是直接的翻译小说诗歌,比如亨利希玻尔和妻子在写下这本小册子之后不久,在爱尔兰乡间定居多年一直在做的就是将许多爱尔兰尚不知名的作品翻译成德文;也可以是这种旅行笔记。广义的旅行写作,便是一种精神译介。
“这冷光穿不透水面,而是粘在了它的表面上,就像水粘在玻璃上,海滩呈现一幅锈色。”
“这是欧洲唯一一个没有对外发起过侵略的民族,唯一没有企图征服外族的民族。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只向外输送牧师、僧侣和传教士。”
这本册子收录的其实是自1954年玻尔第一次造访爱尔兰以来陆续给《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撰写的一系列专栏文。各篇文章标题编辑时略有修改。玻尔在书的前几页简洁地描述了他对这个岛国的第一印象:贫穷,阴雨和天主教。
其中一章叫做“尝试描摹一座城”。描摹的是小镇“Limerick”。英文中Limerick是打油诗的意思。玻尔视之为“Irish joke”。小镇内外的公路上,没有车往来,只有占道的牛羊和上下学的学童。随后不过上午十一点,整座城便空了。他感到“异乡的孤独”,想到“解决旅行中孤独的最简便方法是买东西”,可是寻不到商店。傍晚时分,路过大教堂边的酒馆,才发现人们陆陆续续地出现在街的各个角落。借着爱尔兰黑啤,他才恍然大悟,“周四的上午,整座Limerick城都在大教堂里。爱尔兰人是世界上最虔诚的民族。”
玻尔的笔触向来简练而隽永。他对这座终日不见阳光,海滩如锈迹,水比岩石更硬的西方世界尽头的孤岛有着神秘主义的向往;更对千年来生活在这个岛屿上的这个民族有着难以尽言的倾慕。
“了解了一个令人哀伤的事实:越来越少的孩子将出生在这个岛上。” 这是比带感叹号的陈述句更鲜活更澎湃的告白。
玻尔在德国文化圈的影响自不必说。即便今天,许多德国人对爱尔兰的印象,仍出自玻尔——或他的同僚们:那是一个无比干净的岛,没有地中海咸腻的风,没有阳光下烫脚的细沙滩,没有色彩斑斓的花田、草海、葡萄园,这里只有孤独,永恒的孤独。这是文人们的最爱。
2. 唐 德里罗《名字》
Don Delillo: The Names
坐标:希腊、土耳其。
形式上这是一则完整的谋杀故事。内容上说这表现了作者(或者说文中的叙述者)对语言、古典文化、近东文明的痴迷。精神上说则是一部隐晦的写给希腊和爱琴海的情书。
唐德里罗是写美国的美国大师。这是一条漫长的传统。梅尔维尔和霍桑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就开始站在与欧洲对立的视角上审视这片已经不再新奇的大陆。
世纪之交的亨利 詹姆斯,一篇“Daisy Miller"正式开启了这项母题。随后不论是二三十年代客居巴黎的海明威、菲茨杰拉德们,是战后开始发言的有如诺曼 梅勒, 是六十年代来回横穿北美大陆的”垮掉的一代”们,还是站在后现代废墟上开始重写美国“大书”的作者如菲利普 罗斯,厄普代克,或者唐 德里罗:“美国性”都是他们写作的核心主题,也是他们走上世界文学之神坛的阶梯。
德里罗更出名的代表作是其成名作《白色噪音》(White Noise)。有着英国小说家大卫洛奇(David Lodge)式的幽默和荒诞。而这本《名字》发表于《白色噪音》之前,却被《卫报》和《纽约客》的批评家公认为他实际上的成熟之作。
这是一本关于“名字”的书,一如标题所示。显然不是(或者说不仅是)语义学或者名称学(Onomasiology)意义上的对名字的兴趣;而是一种宽泛的对名词的痴狂。
3. 帕特里克 莱 费尔默
Patrick Leigh Fermer: A Time of Gifts, Roumeli
坐标:中欧、东欧、希腊、土耳其。
费尔默之于英国旅行文学,有如乔伊斯之于爱尔兰文学。
1933年,纳粹席卷欧陆的前夕,十九岁的青年费尔默跨过海峡,踏上了欧洲大陆,开始了一段从荷兰、比利时,经过德国、东欧、希腊,最终抵达伊斯坦布尔的漫长旅途。
旅行的结果是两本大书。“A Time of Gifts”, 和“Roumeli”。
这是难啃的书。语言繁复,句子长,用典多,用词难。
作者在行文的正中某处曾短暂停下,说起自己如何在旅行的途中完成书的草稿:晚上——这也是他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刻——洗漱完毕,就着茶或咖啡,在随便哪个可以书写的角落,点上灯,打开厚厚的笔记本,琢磨起字句。他说自己经常为了造一个完美的句子花上一晚上的时间。也许正是这种对语言的完美主义使得这本书在作者旅行已经结束了快三十年以后才出版。
这是精神历险式的旅行写作范本。
何谓“精神历险”(spiritual adventure)?有别于“physical adventure”,精神历险不限定时空,不要求戏剧性的事态和新奇的事物本身。精神历险只有一个要求:完整的好奇心。
完整的好奇心可以使一次惊心动魄的精神历险发生在最不起眼的角落。不需要闹鬼、谋杀或者事故,费尔默展示了如何平静地站在一座哥特式大教堂的正门口观望,就能完成一次冒险。
他的敏锐不放过旅行中遇到的任何人与事。历史与眼前的纪念碑的关系,不是一种语义学(semantic)的关系,而是一种语用学(pragmatic)的关系。即城堡、宫殿、教堂、废墟,不是指向背后所“埋藏”、“蕴含”的历史故事的一些符号,它们首先是它们本身,和那些历史一样,然后它们才是某种关系。
这便有别于其他大多数旅行写作中的用典。游记中避免不了谈古论今,中西传统皆然。如何避免“掉书袋”?文体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须考虑的是典与游之间的根本关系。费尔默给出了这种新的关系。
4. 布鲁斯 查特文《巴塔哥尼亚高原》、《不安的解剖学》
Bruce Chatwin: In Patagonia, The Anatomy of Restlessness
坐标:南美。
查特文是英国旅行文学历史上又一个大人物。
文体上,拿他和费尔默相比,有如拿海明威与福克纳相比。他好短句,偏爱展示而非分析。
他的虚构故事并不具备说服力。他的逻辑推理缺乏连贯性。他的英文句子也不如费尔默那样丝丝入扣,精益求精。他的天才在于他的直觉与视角。他精简地记录了旅行中遇到的许多人,每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侧面。和费尔默那条传统不同的是,查特文不把每一个不同的人和事都放在一个相同的精神框架里来观望——如同将不同时期不同画家的作品放在同一间展厅里观赏一般——而是在各自当下瞬间的特殊背景下去欣赏、抚摸和理解所有的人与事。
他的《巴塔哥尼亚高原》几乎成了北美南下的背包客的旅行圣经。《不安的解剖学》则收录了他后期的十几篇重要文章。
查特文将伟大的写作者分成两类:一类是挖掘者(digger),如普鲁斯特、卡夫卡、托尔斯泰、福楼拜、左拉;另一类是(mover),如梅尔维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他自己。而费尔默,虽然一直在路上,但或许更应该属于前者。
5. 彼得 海思勒《江城》
Peter Hessler: River Town
坐标:中国,重庆。
二十世纪写中国写出名了的外籍作者固然不少。彼得海思勒算是其中最知名的之一。
海思勒毕业于普林斯顿英文系。九十年代的普林斯顿英文系,独树一帜,收揽了当下一众美国最优秀的小说家,包括红极一时的Joyce Carol Oates。海思勒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写作。毕业后拿到奖金前往牛津深造。前途一切光明,拿到常春藤教职似乎势在必得,研究及教授文学似乎也成为拥有这种教育履历的海思勒不二的选择。然而他选择了来到全然陌生的中国,并且不是上海、广州或者香港,而是深入大陆腹地的江城涪陵。
他一面教授英文——主要是培训英文教师——一面笔耕不辍,为大洋彼岸的大媒体写文章。他的文章逐渐在《纽约时报》、《纽约客》、《波士顿评论》等最大舞台上大展风采。
《甲骨文》(Oracle Bones)是他的成名作。美国东海岸聚集了许多学识渊博的汉学家,然而当他们初次读到这个年轻人在这片古老大地深处写下的一手见闻,还是不免吃了一惊。
《江城》记录了他1996到1998年在涪陵教授英文时的见闻。他与同龄的年轻人交往,同时学习汉语。他不仅教他们莎士比亚、福克纳,也教他们他们自己的文化。他提供见解、视域和理论。然后他也从他们那里获得见解、视域和理论。在他看来,这是在牛津或者哈佛的图书馆里无法得到的东西。
他的文字杂糅了同情和惊奇。他惊讶于他所见闻的贫穷、愚昧、偏狭和暴力,他同情他们,他也惊奇于他们的活力,他们独有的机智与欢愉。
有人考证,海思勒放弃光鲜的常春藤教职,是为了逃避九十年代盛极一时的后殖民主义的话语群。他认为不论是传统的欧洲中心论的、殖民主义的,还是其相反的极端——后殖民主义、多元论、全球主义,都是无聊的、偏狭的。或许理论于他都应该是小心翼翼的,不能草率地宣称概括任何具体的人、事。
对于他,真正复杂而有趣的是那些具体的人和事。而不是站在远处的象牙塔里重建起来的真空幻影。
6. 兹彼格涅夫 赫贝特《海上迷宫》
Labirynt nad morzem ("Labyrinth on the Sea-Shore")
坐标:希腊。
海上的迷宫,这是古老的隐喻。
希腊化时代的地中海文明,曾被比作蹲在一座巨大池塘边上的许多青蛙。地标散落一地,海滩边尽是珍宝。
赫贝特是二十世纪杰出的波兰散文家。他深厚的古典学知识,让他的这本“描绘一个古文明和一片优美的风景的练习册”厚重无比。
而这并不会透过翻译而损失。
7. 约翰 班维尔《布拉格图画》
John Banville: Prague Pictures
坐标:布拉格。
我带着这本书第二次造访布拉格。
在费尔默笔下的长句子里,布拉格阴沉而光辉,充满奇迹。
然而布拉格本身就是一个漂亮的长句子,查理大桥是它的谓语,佩特林山是主语,众多数不尽的巴洛克建筑是宾语。
在欧洲大陆上,布拉格或许是除了巴黎以外经典文学作品中最频繁出现的外景地。光是二十世纪的布拉格就能数出一把大名字:克里玛、哈维尔、昆德拉,往前数到世纪之交有里尔克、卡夫卡,再往前有聂鲁达、哈谢克。
任何一次布拉格之旅都可以是一次拜访这些名字的旅行。并且,旅游业——这个光辉的行业——为当下的我们布置了充足的场所去致敬:就像给party搭设舞池、吧台和酒精。有卡夫卡博物馆;有各种叫里尔克咖啡厅、卡夫卡酒吧之类的抢注册来的商标;当然还有他们笔下出现过的一切:圣维特大教堂、布拉格城堡、鲁道夫音乐厅,等等一切。
班维尔,被很多媒体多次评价为当下爱尔兰写英文写得最漂亮的人,也踏上了一次这样的旅行:访名字。他除了访这些同行和前辈们,也访另一些名字,比如开普勒。他用了另外一本小说专门写开普勒奉命来到时下哈布斯堡帝国的中心布拉格拜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的故事。这个故事也占据了他这本布拉格游记的大部分。
他也有很多现在普通拜访者不能有的特权:比如来自布拉格大学文学教授的 一手资料和充满激情的讲述;比如八十年代仍然残留在这座锈迹斑斑的古城中的共产主义。
他既写城里街巷角落躲藏着的卡夫卡阴影,也写饭馆里难吃的捷克菜肴。他用绵软的笔触,触摸这座城市的锈迹和伤痕。
他说,站在查理大桥上,突然觉得活在此刻很美好,此刻在布拉格。不可思议。
8. 罗伯特 斯蒂文斯《爱丁堡日记》
Robert Louis Stevenson: Edinburgh: Picturesque Notes
坐标:爱丁堡。
斯蒂文森的这部爱丁堡笔记,是二十世纪几乎所有重要英文旅行作者的启蒙书。
他的文字形式的爱丁堡笔记,就像特纳线条与图形形式的爱丁堡笔记。他们都画废墟:刻画关系、召唤历史。
他教会后来二十世纪数不尽的用英文写作的旅行者们,如何写建筑,如何写声音,如何写社会关系,如何写人群,如何写山坡,如何写海。
因为这一切,爱丁堡这座“北方的都城”都有。
其他一些喜欢的:
10. 奥尔罕 帕慕克:《伊斯坦布尔》,坐标:伊斯坦布尔
11. Laurie Lee: As I Walked Out One Midsummer Morning,坐标:英格兰。
12. The Old Ways by Robert Macfarlane,坐标:不列颠岛、西欧、巴勒斯坦、西藏。
13. Naples '44 by Norman Lewis, 坐标:意大利,那不勒斯。
14. Coasting by Jonathan Raban,坐标:不列颠岛。
15. Travels with Charley: In Search of America by John Steinbeck,坐标:美国。

16. Homage to Catalonia by George Orwell,坐标:加泰罗尼亚。
17. Ian McEwan: The Comfort of Strangers,坐标:威尼斯。
18. Ernest Hemingway: Death in the Afternoon, The Sun Also Rises,坐标:安达卢西亚。
19. Into the Wild: John Krakauer,坐标:美国西部、阿拉斯加
3/6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尾页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