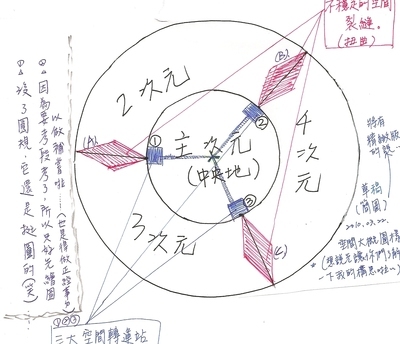主要参考资料:
1. 托比•胡弗:《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第七章 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八章 中国的科学与社会组织;
2. 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三联书店 2009 导论与总结部分
3. 林毅夫:《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年7月第44卷 第4期
4. 陈炎:《儒家与道家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制约——兼答“李约瑟难题”》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 第1期
对于历史问题的原因探究,托夫勒在其《第三次浪潮》中提出了些怀疑,在论及工业革命时,托夫勒就历史推动力的复杂性和深刻性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任何对工业革命原因的探索都是徒劳的,因为它没有一个简单的和主要的原因:技术本身不是推动历史的力量;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本身也不是;阶级斗争也不是;历史也不仅仅是生态变化、人口趋势统计或者交通工具发明创造的记录。单单用经济因素也不能说明这个或其他历史时间。这里没有超乎相互依赖的可变因素之上的其他‘独立不变因素’。这里只有相互关联的可变因素,其复杂性深不可测。”
这段带点不可知论意味的论述揭示出了任何分析阐释在历史的宏大与复杂面前所显现的苍白。近代科学为何没有发源于中国,其原因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丝毫不会亚于工业革命发生的原因。因此,按照托夫勒的观点,探索李约瑟难题的答案完全有可能是徒劳无功的。
另一方面,如席文(Nathan Sivin)所言,历史上没有发生的事情比比皆是,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都去追究个中缘由,“李约瑟难题类似于为什么你的名字没有在今天报纸第三版出现的问题一样,它属于历史学家所不可能直接回答,因此也不会去研究的无限多问题之一,而那些问题可以说是无所不包的”。
席文的质疑应当说是富有见地的,但是李约瑟难题还是引来了学者的关注和尝试,尤其是中国学者,如任鸿隽(《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梁启超、蒋方震、冯友兰(《Why China has no Science-an Interpretation of theHistory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ese Philosophy》)、竺可桢(《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究其缘由,我认为一来近代中国的丧权辱国、内忧外患促使一大批中国的知识分子,以一种饱含希冀也带着些许痛切的目光去审视这个并非纯粹的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辉煌的中国古代文明与中国近代在科技方面的落后形成了鲜明的比照,如李约瑟认为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世纪之间,“在将自然知识应用于实际的人类需求方面,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更为有效”,而西方文明在科学领域的崛起与中国的没落似乎只在一个及其有限的历史维度内骤然发生,将问题以这种前后落差的悖论形态展现出来似乎更具理论探讨的价值。
前述第一点只不过是描述了中国学者带有民族情感倾向的诉求,此不赘言;而第二点理由,却值得推敲,尽管李约瑟使用了“将自然科学应用于实际的人类需求”这样有些含糊不清的表述,但其实际指向依然是明显的,即中国文明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世纪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应用型的工艺技术。然而,中国文明在15世纪后的落后更多是科学理论层面。之前的“技术”与之后的“科学”,两者是否具有直接的可比性?
我认为,科学区别于技术的特征是不容忽视的。“科学是相对于技艺(techne)的认知(episteme),它具有思辨性,它总是猜想新实体、新过程和新机制的存在,更不用说可能存在的新世界了”(Huff 第229页),从一个更为浅显的视角来看,“科学与如何描述、解释和思考这个世界相关,而不是与如何使劳动更容易或如何控制自然相关”(Huff 第229页),但是,“技术发明几乎总是缺乏哲学和形而上学的蕴涵,而这些蕴涵却是科学研究的固有成分”(Huff第229页)。
因而,前述问题实有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之嫌。中国文明在15世纪之前的技术领先和之后的科学落后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反差,如席文所言,“早期技术的成败,并不取决于它是否有效地运用了科学提供的知识”,“只有在近代,各种各样的科学与技术的结合才变得密切起来”,这意味着,中华文明在早期的技术领先,并不必然暗含了中华文明在科学上同样领先的前提。我们完全可以假设,中华文明在科学上的落后是由来已久的,只是基于某种原因,中华文明的技术在早期处于优势地位。以此作为看待问题的基本视角,很多所谓的难题、悖理(puzzle, paradox)其实都会自动消解。由此,我们似乎更应将上述问题分而论之(当然,将这两个问题不可能完全割裂开),即:
1、工艺技术层面:中国文明为何在早期获得了技术上的领先;
2、科学理论层面:中国文明的科学是否如其工艺技术一般,曾领先于西方文明或阿拉伯文明;以及近代科学为何没有在中国出现。
中国文明在早期技术领域的优势地位自不待言,其中原因却值得玩味。我赞同席文对于早期技术与科学之间的关系的论断——即早期技术的成败,并不取决于它是否有效地运用了科学提供的知识,这意味着,早期技术的获得,并不基于科学的抽象理论基础,也非来源于科学理论的理性指导,它实质上是一种以经验为导向的试错过程:“在18 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前,不管是在中国或是西方世界,新技术的发明一般来自于直接从事生产的工匠或是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偶然的偏离常规方式的试错的结果,”而我们假设试错发现新技术的概率是一定的,则人口规模庞大的古代中国在新技术的发现方面就有了其他地区所无可比拟的优势;另外,“中国古代官员的流动,农书的印发与产品和劳动力的自由市场流通等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则间接加速了新技术的扩散”。由此,中国文明在一个相对长的历史跨度内维持着自身在技术上的优势地位。
这种“试错概率”理论需要回应一个最为直接的质疑——为何试错在17、18世纪之后无法再让中国文明保持其传统优势。对此,林毅夫教授也给了颇为完满的回答,“这种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方式,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技术发明的空间将会越来越小,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可避免地终将趋于停滞” 。到了17、18世纪,技术发展的瓶颈已不是经验性的试错所能突破,必须经由基础科学的努力,在理性认知的层面加深对于自然界的认识,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去拓展新技术发展的空间,而中国的科学没能在17、18世纪达到此种水平。
按照此种进路,分析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第二个问题,即中国文明的科学理论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的发展及地位,或者说为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没能在17、18世纪达到某种水平,以突破经验试错所无法突破的瓶颈。
首先,根据胡弗的观点,“中国的科学自大约11世纪以来不仅落后于西方,而且落后于阿拉伯”(Huff 第230页)。在书中,胡弗细致地考察了中国在近代科学的传统核心研究领域——天文学、几何学、三角学、物理学、光学和数学,认为中国并未在这些领域取得领先于西方或阿拉伯文明的成就,而冯友兰先生则更为直截了当地写道“中国的落后是因为中国没有科学”。我们似乎可以认为,中国科学的落后是一以贯之的历史进程,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出现这一事实在这样的语境之下也显得顺理成章,追问“近代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似乎没有意义,某种程度上,这个问题和“近代科学革命为何没有在马达加斯加发生”或者“为什么你的名字没有在今天报纸第三版出现”的问题一样,属于席文所谓的历史学家所不可能直接回答,因此也不会去研究的无限多问题之一。
然而,胡弗在书中对于席文的质疑进行了批评(尽管我觉得这种批评带有伦理意味和价值预判,但依然不失为精彩的论述)。胡弗认为我们应当承认这一假定:“在所有的文明的每一时代中,至少有一些人曾追寻过关于人和自然的真理,并且那些经受住了理性批判和经验比较的结论代表了普适真理的趋同秩序”(Huff 第235页),既然这种追寻是东西方文明都曾有过的,那为何最终欧洲产生了科学革命而中国没有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两人都努力试图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第三版,那么,没有成功上报的那个人失败的原因就是值得追寻的。科学革命亦是如此,我们“可以没有偏见地努力确定那些社会、宗教、哲学、法律、经济和政治因素——它们推动或阻碍了世界上各种社会和文明中的科学思想的智识发展”(Huff 第235页),“否决如下疑问:为何一个社会群体或另一个——一个社会、文明或其他——没有沿着一条特殊的文化和经济发展路线,尤其是通向更高水平的科学成就的经济成就的路线前进,无异于道德责难”(Huff 第236页)。
因此,“近代科学为何没有产生于中国”,同样是社会科学所应当研究和解释的现象。
关于前述问题,林毅夫教授认为,可以归结到一点,即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这一导向性极强的特殊激励。“中国的科举制度所提供的特殊激励机制,使得有天赋、充满好奇心的天才无心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等对科学革命来讲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本,因而,对自然现象的发现仅能停留在依靠偶然观察的原始科学的阶段,不能质变为依靠数学和控制实验的现代科学。”,林教授的解释以人力资本为中心,“官本位”与“学而优则仕”的普遍理念使得在古代中国,仕途在任何意义上都是有才能抱负者的康庄大道;然而,由于科举考试的内容被限缩在一定范围(儒家经典和历史),而这种考试又以带有智力测验性质的高级文字游戏为载体,最终使得中国有较高天赋的人都埋首故纸堆,专注于科举应试。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的激励的缺乏使得中国不可能拥有充足且优质的人力资本去推动近代科学革命。
应当说,以上观点是逻辑清晰且值得称道的,但我更倾向于把科举制度视为解释的一个因素而非根本原因。且不论科举制度的出现已经是隋唐年间的事,科举制度的发展也是从针对不同人才进行不同科目考试,到将考试范围限缩到以“进士科”为主,这种限缩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似乎也值得探究。当然,我并不是想进行“十万个为什么”似的层层溯因,无限度的穷究是没有意义的,但科举制度毕竟是人为创立的一项制度,将溯因停留在这一层面似乎有些太过浅显了;更重要的是,科举制度出现之前中国文明已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历程,而相比于欧洲文明,中国文明在科举产生之前同样缺乏如古希腊文明一般的科学与理性精神,而此问题是科举制度的解释所难以涵盖的。有观点认为,现代科学革命实由古希腊数理科学传统的复兴所触发,“公元前3世纪的亚历山大数理科学已经决定性地将西方与中国科学分别开来;从此再往前追溯,则可以见到,西方与中国科学的分野其实早在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数学与哲学传统形成之际就已经决定,公元前5至4世纪间的新普罗米修斯革命是西方与中国科学的真正分水岭。”
如果西方文明早在公元前就已经隐含了能触发近代科学的基因,那出现在公元6世纪以后的中国科举制度则不可能是中西文明走向殊途的根本缘由,这其中必然有更为原始、深刻的原因值得去发掘。
在《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一书中,胡弗论述了几个方面的原因——从法律制度与理念、行政体系、教育和考试体系、语言到国人的思维方式。
法律与政治方面,胡弗认为,在中世纪盛期,欧洲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和智识革命,这场革命的意义在于,它重新定义了所有领域的社会组织的性质。由此,法律上自治的新团体(包括居民社区、城镇、大学、经济利益团体和职业行会)出现了。胡弗认为此种变革对于科学革命的意义在于它促使了一块沃土的产生,“中立空间——一个免于宗教和政治审查干扰的相对独立的空间——开始崭露头角”(Huff 第238页),由此,通往智识自由的大门被打开了。胡弗对于中西文明在这一时期的比较是以“自治空间”为核心的,然而,考察同时期的中国,却会发现自治空间毫无生发的迹象:无论是在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还是强调等级、集体责任的法律文化中,抑或是在科举考试引导下的功利教育体系里,自治空间都没有产生的驱动力或是生存的空间。
对于上述现象,我认为其实质原因在于,中国古代的政治与法律有着对于“克己复礼”的内在强调,例如,中国文明的官方意识形态要求臣民按照君王的意愿遵循既定的孝道和谦恭要求,以维持帝国的安宁与和谐,而这种强调抑制了任何自主思想和行动的产生与发展。
教育和考试体系方面,不同于作为自主自治机关的欧洲大学,中国的书院从来都不是拥有独立学术传统的自治机构,在官本位的社会背景以及科举制度的强势引导下之下,中国的教育全以科举考试为中心,“无私利性的学术研究的兴趣让位于科举及第的强烈愿望”(Huff 第299页);而儒家意识形态的绝对统治,也阻碍了适于研究自然现象的方法论的创立,总之,“科学研究被放逐在了中国社会的边缘”(Huff 第269页)。
语言方面,由于中国悠久的文学传统,汉字作为个体符号具有非常广泛的暗含意义,而“中国古代文人习惯使用多种古老的隐喻、典故、陈词滥调,以及名声不好的未直接标明出处的古代作家的抄本”(Huff 第274页)。这种语言的特性以及语言的使用习惯毫无疑问与科学研究所要求的简单明确的表达方式有相违背。
胡弗最后论及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这一极具理论张力的问题,我认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胡弗拓展得最不充分,然而却是最基本,最深刻的方面。思维方式及民族心理结构作为一种贯穿始终的强大力量,一直站在诸如科举制度、政治体制、法律理念等等具体因素的幕后,其所牵动的方方面面都能作为李约瑟难题的注脚。我认为,对于这一点的分析可以引申出三个具体的方面:
1. 关怀现世,不务“玄虚”的“实用理性”精神:
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名作《全球通史》中谈到“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在任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文明,这根源于中国文明独特的现世主义”。我认为,儒家思想以伦理为中心,以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作为考虑问题的基点;其带有浓厚的实用理性精神,从“修身”、“齐家”到“治国”直至“平天下”,儒家最终还是皈依于现世的人伦世界,而无关乎超然的哲思,也无关乎对人与自然的思考。儒家一直都回避抽象的形而上玄思,对于许多科学应当关注的事物,采取“存而不论”的回避态度。如“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子不语怪、力、乱、神。”。不难发现,儒家学者素来主张学以致用、知行合一,而不务玄虚空灵之学问,但是,早期的科学素来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因而注重思辨、理论的科学在儒家思想所支配的思维结构中便难觅一席之地,在儒家思想大行其道的时代,那些既非功利,又注重抽象性思维的科学理论无从产生。
实用理性精神建构出了以伦理为中心的中国古代社会,现世关怀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正如李泽厚所指出,“实用理性”关注于现实生活,它不作纯粹抽象的思辨,也不让非理性的情欲横行,事事强调‘实用’、‘实际’和‘实行’,满足于解决问题经验论的思维水平,主张以理节情的行为模式,对人生世事采取一种既冷静又理智的生活态度。 受实用理性支配的心理结果和思维方式,很难超越“经验论的思维水平”,这也正好应合了林毅夫教授关于中国科技在近代落后的原因的解释——即经验性的试错空间愈趋狭小。
2. 脱离客观自然,直面精神世界的知识论倾向:
中国的思想者一贯注重内省,注重精神世界的追求与升华,而轻视对客观自然的探究。《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白虎通义》谓 “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不知也”,一切的认识都能够通过“心”与“性”的觉悟来获得, 此因中国古代所重之修身之学无关于客观自然,“它通过文字的媒介,敲开心灵的混沌,激发道德的潜能,将文字中所涵的旨意,化为行动,提升人格”,此亦是“荀子所谓的‘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的君子之学”。诚如冯友兰先生所言,“中国的哲学家们,没有科学的确实性的需要,他们所要知道的只是他们自己而已,同样地,哲学家们也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所要征服的也仅是他们自己”。
3. 中国式的关联性思维模式:
胡弗认为,“中国文人所倾向使用的语言表达形式增强和保持了关联性或类比性思维模式” (Huff 第279页),这使得古代中国从未能超越以二元对立为基础的关联性思维方式,从而走上对科学理论有所裨益的因果思维之路,这也是对于中国古代抽象的理论科学发展的障碍之一。
综上,我认为,关怀现世的“实用理性”精神、脱离客观自然而注重内省的知识论倾向,以及未走上因果之路的关联性思维模式是国人思维方式及心理结构的三个重要方面,内生于此三个因素的要义往往与现代科学所要求之精神相违背。
4/4 首页 上一页 2 3 4 爱华网
爱华网